
豆腐巷里忆童年
□王玉芹
豆腐巷街在古运河东岸,北起东风西路,南至运河堤,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偏斜的街巷。这里曾是三面被运河水环绕的小河圈,因靠近城池,且有通往河北的公路,自古便是德州城吞吐量较大的码头,见证过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我的童年,就安放在这条老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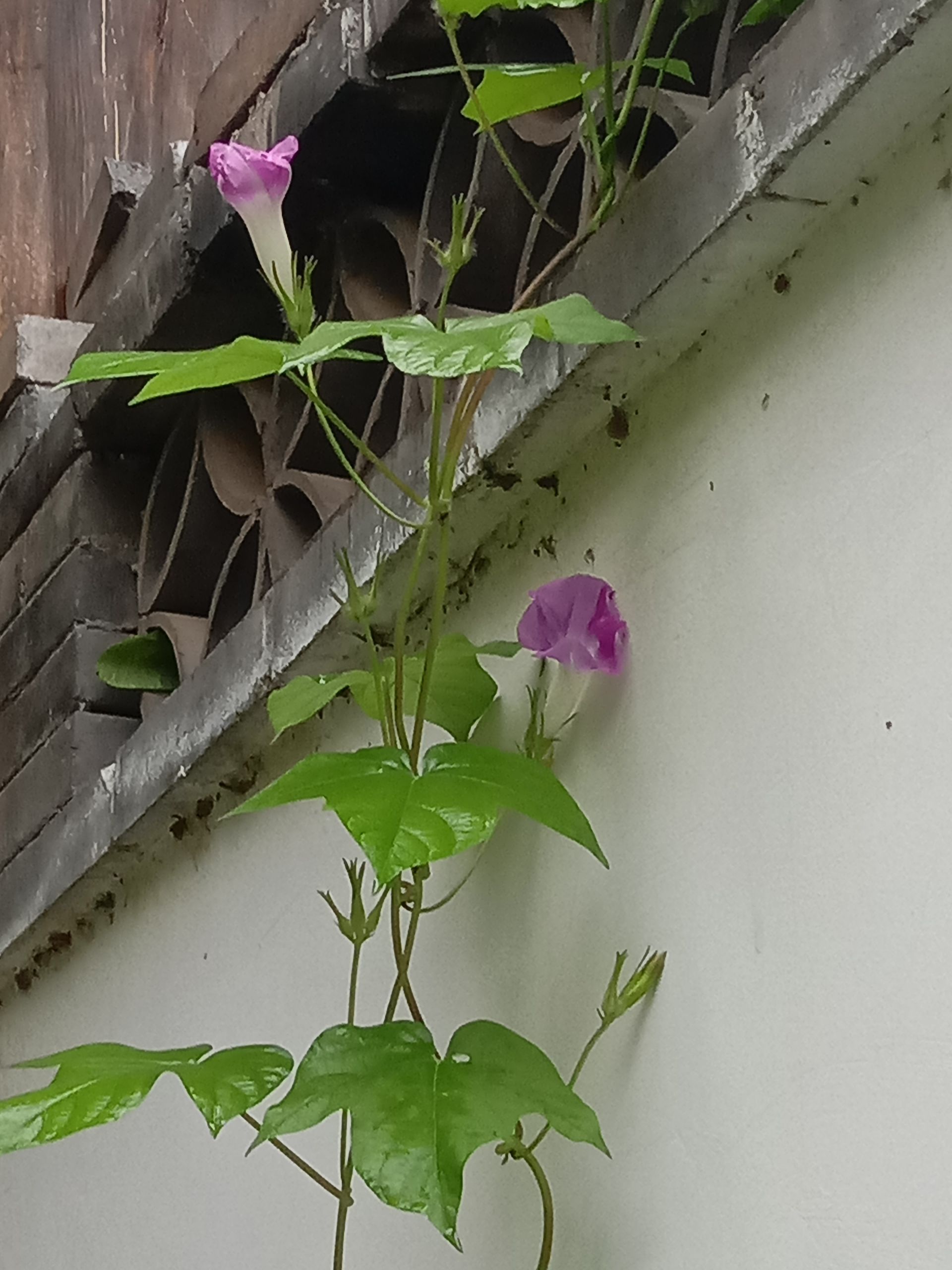
巷子不宽,一条斜斜的上坡路贯穿其间。巷口有个土台子,旁边散落着几块大石头。小时候,我们常把土台子当作舞台,在上面唱歌跳舞。唱得最多的是《雷锋叔叔望着我们笑》,跳得最多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曾问过妈妈土台子的来历,妈妈说:“古时候,这里是座关帝庙。” 农历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八月十五等传统节日,豆腐巷的居民会在庙门上挂起红灯笼,叩拜关老爷,祈求保佑。后来,庙宇因年久失修变得岌岌可危,渐渐成了危房,最终被拆除。只剩下这土台子和几块石头,供居民乘凉、闲谈,追忆往昔。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风路拓宽,那个土台子也被拆除。从此,豆腐巷关帝庙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也渐渐淡忘了它。
整条巷子最引以为傲的,便只剩下街中心下坡处的那口甜水井了。说起这口井,满满的回忆便涌上心头。它不像别的井那样深不见底,却每天泛着汩汩的水光,宛如小龙女含泪的眼眸。井口围着厚重的青石板,被磨得光滑发亮;井绳在石板边缘勒出深深的沟痕,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每天天刚蒙蒙亮,巷子里的宁静就被 “吱呀” 的开门声和水桶碰撞的清脆声响打破。邻居们提着水桶,排队打水。大人们熟练地放下井绳,木桶 “扑通” 一声沉入井底,再双手交替,稳稳地将装满清水的桶提上来。
井水流淌在桶中,清澈见底,带着一丝丝沁人心脾的甘甜。我们这些小孩子,跟在大人身后,最爱趴在井边张望 —— 看井水映出天上的流云,看自己的小脸蛋在水中晃来晃去。偶尔,还能得到大人递来的一小瓢井水,那甘甜的滋味会从舌尖蔓延到心底。记忆中有一次,前面打水的哥哥笑着从刚提上来的井水里,舀出一小瓢递给我。我双手捧着瓢沿,“咕咚咕咚” 喝下去,那股甘甜真的从舌尖一直甜到心里,瞬间驱散了夏日的炎热。井水顺着嘴角流到脖子上,我抹了一把,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起来。那时候每家水桶里都放一个小瓢,是担心担水过程中,水会晃出来。
这口井是德州城的名井之一,水质独特甘洌,名声远扬运河上下。用它做出的豆腐更是一绝 —— 磨浆、煮浆、点卤…… 每一步都离不开这口井的水。点出来的豆腐,白白嫩嫩,豆香浓郁,口感绵密。
甜水井不仅滋养着巷子里的人,更成就了豆腐巷的美名。巷子里有户罗姓人家,用这井水点豆腐,手艺出了名的好。做出的豆腐口味独特,质优价廉。清晨,豆腐摊前总是排着长队,那股独有的豆香,能飘遍整条巷子。其名声很快传遍古城,故而又引来了几家豆腐作坊在此落户,逐渐形成了豆腐作坊和市场聚集地,“豆腐巷” 也因此得名。直到20世纪60年代,豆腐巷街老李家的 “蹶腚豆腐”,在德州城仍是名气最大的。
德州自古盛产大西瓜。每到西瓜上市的季节,妈妈总会用刚从井里打来的水,把西瓜泡上半晌。待西瓜凉透,全家人围坐在桌前,翡翠般的西瓜在妈妈手起刀落间,变成了红瓤黑子,让我们垂涎欲滴。入口的瞬间,那股清凉甘甜沁人心脾。可西瓜不是随便吃的,妈妈总会均匀地分给我们姐弟。记忆中,大姐总是吃得很慢很慢 —— 其实,她是故意少吃一些,留给嘴馋的弟弟妹妹多吃一点。想起小时候的姐弟情深,泪水便会不自觉地模糊了双眼。
后来,老街改造,自来水管通到了家家户户。没人再去井里打水,井水也就渐渐枯竭了。但那口井、那甘甜的井水,还有清晨排队打水的热闹场景,都成了我记忆深处最温柔的画面。因为在我心里,它早已不是一口井那么简单 —— 它是故乡的符号,是邻里的温情,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童年印记。直到现在,一想起它,心里就会泛起一阵清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趴在井边,盼着喝一口井水的童年午后。
如今,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佰利金湖城”,占据了豆腐巷的旧址。从此,豆腐巷的名字,就只停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了。可是,每到夏天西瓜上市的时候,我还会想起妈妈用那口井水浸泡过的西瓜,想起我们姐弟围坐一起等吃西瓜的情景,心里依旧会涌出那股化不开的清甜。

作者简介: 王玉芹,女,德州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德州市诗词协会会员。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