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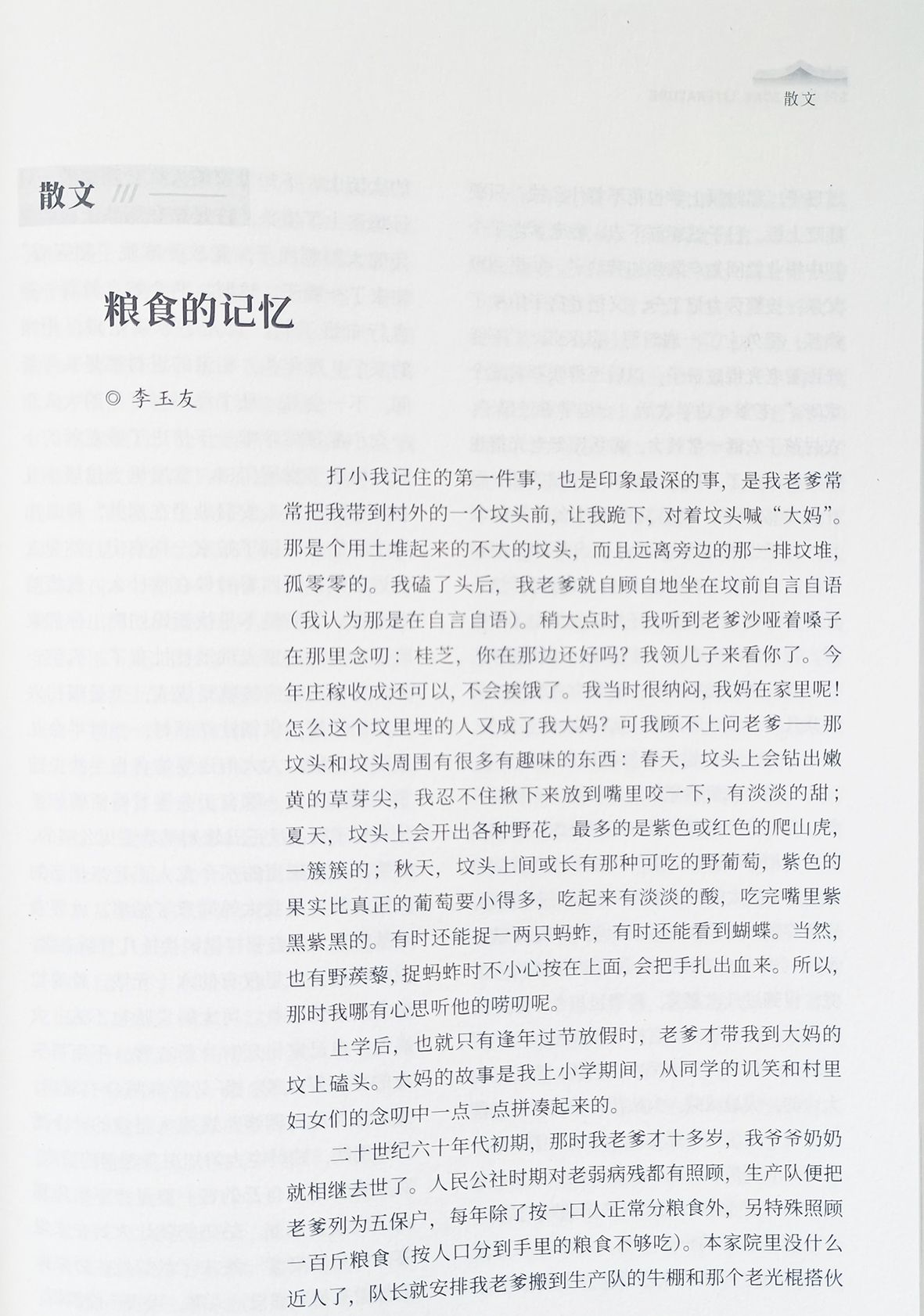
粮食的记忆
□李玉友
打小我记住的第一件事,也是印象最深的事,是我老爹常常把我带到村外的一个坟头前,让我跪下,对着坟头喊“大妈”。那是个用土堆起来的不大的坟头,而且远离旁边的那一排坟堆,孤零零的。我磕了头后,我老爹就自顾自地坐在坟前自言自语(我认为那是在自言自语)。稍大点时,我听到老爹沙哑着嗓子在那里念叨:桂芝,你在那边还好吗?我领儿子来看你了。今年庄稼收成还可以,不会挨饿了。我当时很纳闷,我妈在家里呢!怎么这个坟里埋的人又成了我大妈?可我顾不上问老爹——那坟头和坟头周围有很多有趣味的东西:春天,坟头上会钻出嫩黄的草芽尖,我忍不住揪下来放到嘴里咬一下,有淡淡的甜;夏天,坟头上会开出各种野花,最多的是紫色或红色的爬山虎,一簇簇的;秋天,坟头上间或长有那种可吃的野葡萄,紫色的果实比真正的葡萄要小得多,吃起来有淡淡的酸,吃完嘴里紫黑紫黑的。有时还能捉一两只蚂蚱,有时还能看到蝴蝶。当然,也有野蒺藜,捉蚂蚱时不小心按在上面,会把手扎出血来。所以,那时我哪有心思听他的唠叨呢。
上学后,也就只有逢年过节放假时,老爹才带我到大妈的坟上磕头。大妈的故事是我上小学期间,从同学的讥笑和村里妇女们的念叨中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老爹才十多岁,我爷爷奶奶就相继去世了。人民公社时期对老弱病残都有照顾,生产队便把老爹列为五保户,每年除了按一口人正常分粮食外,另特殊照顾一百斤粮食(按人口分到手里的粮食不够吃)。本家院里没什么近人了,队长就安排我老爹搬到生产队的牛棚和那个老光棍搭伙过日子。那时候上学也花不着什么钱,只要能吃上饭,日子就能混下去。我老爹念了个初中毕业就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了。队里照顾父亲,按整劳力记工分,又把老房子给换了换顶,里外上了一遍新泥。队长说:“不能光跟着老光棍过日子,以后还得张罗着成个家呀。”老爹一边学农活,一边学着过日子。农村孩子农活一学就会,做饭跟着老光棍也学得差不多了,只是以前每年照顾的那一百斤粮食取消了,家里又没有什么进钱的项目,日子也就没啥大起色。几年下来,眼看同龄人有的娶上媳妇当了爹,而我老爹这儿还没人给提亲。后来,还是队长给出了个主意,找公社的人说了一下情况,让我老爹去当了兵。那时候在农村,想要有点出息,去当兵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实际上,队长是想,我老爹当上兵,说个媳妇就八九不离十了。
可这办法到我老爹这里不灵了。当兵三年,也有几个给我老爹介绍对象的,但都没成。有相中老爹人才的,可架不住女孩父母嫌老爹家里太穷,硬是给拦住了。三年期满,老爹穿着一身摘了红五星和领章的绿军装复员回村来了。听说那时我老爹在部队入了党,得到过几次嘉奖,还当过班长。回到生产队后,老爹就名正言顺地担任了村里的民兵连长。穿着一身绿军衣的老爹,个子高高大大的,很是威武。大伙帮衬着把老房子翻修了一下,这才总算有人来家相亲了。这个来相亲的就是躺在坟头里的大妈。妇女们总是津津乐道地说起我大妈来相亲时的故事。
那是秋末的一个下午,出工的人已走得没了影,西斜的太阳懒洋洋地照在寂静的大街上。不知谁家的大红公鸡追着一只母鸡飞上了墙头,许是站在墙头上被明晃晃的太阳刺激了,竟放开喉咙“喔喔喔”地来了一嗓子。这时,两个妇女骑着一辆自行车进了村。有人小声嘀咕说,相亲的来了!那年头,相亲的进村都是头号新闻。不一会儿,几个没出村干活的大人和一众小屁孩就呼啦一下挤进了我老爹的小院,堵在了堂屋门口。堂屋里一位矮小且衣着普通的女人安静地坐在那儿,像是出嫁了的姑娘回到了娘家一样安宁。她见人们进屋东瞅瞅西看看像在找什么,就笑嘻嘻地说,你们是不是找新媳妇啊,你们来晚了一步,人家去供销社扯布了。人们一听,明白这位应该就是媒人,于是很扫兴地退出了屋。供销社在邻村,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的。大人们还要忙各自手头上的事,得挣工分,哪有工夫等着看新媳妇长什么样子呢? 反正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的。其实,坐在屋里的那个女人正是来相亲的大妈。媒人看我大妈同意了婚事,就要我老爹带着大妈去邻村供销社扯几身新衣裳。我老爹揣上家里仅有的六十元钱,就要拉着大妈去供销社。可大妈说啥也不去。大妈说,自己家里还有身新衣裳,不用再买新的了。媒人说,好歹得有两身衣裳呀,要不这叫怎么回事?这媒人是我的一个远房姑奶奶,她料定大妈知道我老爹的家底,买衣裳就是花自己的钱,要是拉下饥荒那进了门就得还账。姑奶奶就让大妈在家里等,她和我老爹一块去了供销社。后来人们知道真相后都说,人啊,可真不能貌相。
没经过任何波折,我大妈顺利地嫁了过来。尽管我老爹和我大妈站在一起是那么不般配,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恩爱。日子因为结婚借了些钱更拮据了些,老爹和大妈的压力可想而知。不过,那时人们的日子都差不多,除了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地干活,其他的也真没啥想头。
这年秋后,公社组织各村出河工。我们那里把政府安排下来的挖河修沟等水利工程叫作“出河工”。每次出河工的地点都不固定,有远有近,远的要到外县,走百十里路;近的就在本公社的一个村。村里的男劳力轮流排号出河工。虽然出河工累些,有的人甚至坚持不下来,但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出河工的,因为队上管饭,记整劳力工分,这样可以省下家里一个人的口粮,并且出河工时吃饭管饱,还全是玉米面窝头。每次出河工我老爹都有份,他是民兵连连长,是带队的。
这年出河工是在本公社挖一条生产沟。施工比较顺利,比计划的时间提前两天完工了。从施工地往回撤时,队上带去的玉米面还剩了一些,按平常做法,虽然出河工的人回村了,但还在施工期,还是可以吃出河工的饭。所以,这剩下的玉米面就会平均分给出河工的劳力,人人有份。这往回带玉米面的活一般是我老爹来干。回到村里,老爹把玉米面放到饲养棚老光棍那儿,找来秤,让大家各带家什一块来分。连我老爹在内二十二个人,玉米面连袋子共七十八斤,袋子折一斤,按每人三斤半分。我老爹是负责掌秤杆的。俗话说,一秤来百秤去,每家三斤半称走后,我老爹掂量了一下口袋,叹了一口气,拎着口袋回家了。口袋是生产队的,用完得还回去。
能分三斤半玉米面的事大妈已经从旁人口中知道了。老爹进了家门,大妈欢喜地从老爹手中接过口袋,掂了掂,脸上的笑容就不见了:“你们分的不是三斤半吗?这些有三斤半?加上口袋差不多!”老爹自知理亏,为自己分辩:“都是平秤,分到最后就剩这些了,你说怎么办?”大妈有些愤愤不平:“你还是个带队的,一样分粮,咱不多分也不能少分啊!吃亏要吃在明处。”大妈说着,把玉米面倒进一个大盆里,又挽了挽袖口,拿起口袋就像翻猪肠子一样把口袋翻了过来。大妈提着口袋用笤帚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把沾在上边的稀薄的玉米面扫了下来,又仔细瞅了瞅口袋,发现这个布口袋底上还沾着一层糊糊。大妈就拿过菜刀,一点一点地把口袋底上那些糊糊剜了下来,然后看了看这条被她好一顿收拾的口袋,才心有不甘地翻过口袋,叠好,放在一边。大妈把这些玉米面掺上一些家里的玉米面,做成了玉米面饼子,贴到锅里。吃饭的时候,老爹拿起刚出锅的饼子咬了一口就放下了,皱着眉头说:“这么牙碜,怎么吃呀!”老爹只喝了一碗粥就拿上口袋出去了。大妈使劲咽下嘴里嚼来嚼去的饼子,对老爹的背影说:“嫌牙碜你把那少给的玉米面弄回来呀。”
得知大妈出事时,老爹正和生产队队长在牲口棚里商量借冬闲开荒地的事呢。是邻居去我家串门,发现大妈躺在地上打滚,嘴里吐着白沫,脸色发青,这才着急忙慌地跑来找我老爹。老爹一听拔腿就往家里跑。队长一看这情况,忙吆喝老光棍套上大车到俺家拉上大妈就往公社医院赶。到公社医院十多里地,我老爹在车上抱着我大妈,一个劲地催赶车的老光棍:“快呀!快呀!”老光棍也不答话,只是把鞭子甩得叭叭的,那头拉车的驴屁股上印了好多鞭痕。大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来颠去,我大妈好像没有感觉一样,安稳地躺在我老爹怀里。
公社医院的大夫给大妈打了两针,没敢留人,就派人护送着坐拖拉机去了县医院。到了县医院,急救的医生就没让往下抬人,翻了翻我大妈的眼皮,拿手电照了照,摸了摸脉,说了句,人不行了,回去吧。说完转身走了。我老爹傻了似的待在医院抱着大妈不肯走。
公社很重视这件事,派公安来村里调查。穿着白上衣蓝裤子,戴着白大盖帽的公安在村里调查了一天,把那条布口袋也带了回去。几天后传来消息,说是那条布口袋上沾染有剧毒农药1605。直到这时,队长才一跺脚,骂了一句粗话:“这条口袋秋里种麦子时装过拌了1605的麦种啊!怎么用它装人吃的粮食呢!”
没了大妈,老爹又过上了单身生活。一年后,我妈随我姥爷从东北回到了老家山东,因惦记着回老家,姥爷没敢在东北给我妈找婆家,结果我妈回到山东都三十岁了。我老爹是穷了些,可架不住我妈相中了老爹的样子,拗着姥爷嫁了过来,这才有了我。
那几年,老爹兼任了生产队队长,连着几年利用农闲带着大伙开荒地。我们这里是平原地区,盐碱、涝洼的撂荒地多,要是修台田、挖排水沟,再多上点儿圈肥,荒地也是能慢慢养成好地的。荒地里打下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村民能分到手的粮食就多了些,大家脸上的笑容也就多了起来。那年麦收后,按数交完公粮,社员们对着剩下的那一大堆金灿灿的麦粒说,从没见过队里能有这么多麦子啊!一身土、一身汗,泥猴似的老爹,站在那堆麦粒前,笑着笑着,突然“桂芝呀——”大叫了一嗓子,就一头扎在麦粒堆上,号啕大哭起来。社员们说,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得那么伤心。
没过几年,村里就把地分给各家各户种了,那些盐碱、涝洼地也都让村民种成了好地。从那以后,吃粮再也不发愁了,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后来我上了大学,进了城。在城里娶妻生子,安安稳稳地享受着富足的生活。我老爹和我妈恋着老家那几亩地,不肯到城里来享福——其实,在老家有吃有喝地过着田园生活,也许更让他们惬意。有时看见妻子准备倒掉孩子剩在碗里的饭,我会端起碗把饭扒进嘴里,并忍不住说孩子几句,而妻子则每次都朝我翻白眼,嫌我多事。我只能叹一口气。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大妈的故事,要不要给妻子和儿子说。说了他们会信吗?有时连我自己也恍惚,大妈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呢?
(原文载于2025年10月下半月刊《特区文学》)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