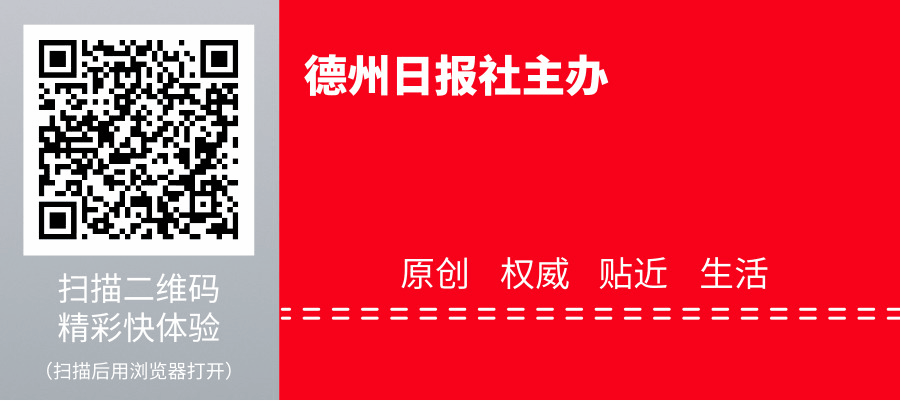清 明 祭
文 | 苏艳
沿着春天迟缓的脚步
走进清明
今天 不焚香跪拜不烧纸钱
只点一支蜡烛引燃燎原的思念
所有的言语都抚不平
锥心的刺痛
悼念的泪水落进汉江
压抑的呜咽拍堤卷岸
每一块崭新的墓碑
都镌刻着对生命的不舍
如果一场雨不足以祭奠
就让我们
把通往天堂的路用花瓣铺满
再把哀思分成两半
一半遥慰先烈
一半抚慰苍生
寒 食
文 | 刘拥军
又到一年寒食节,
荒原野陌笼幽烟。
飞灰柳絮坟前舞,
碧草青天梦里联。
灵影常从来者出,
果只每向落红悬。
分明看是梨花雪,
泪眼漫天认纸钱。
清明小雨
文 | 杨树青
连布层云压柳低,
两帘玉雪挂城西。
娥眉粉面点珠碎,
绿水涟心飞镜迷。
万物欣承春草露,
群阴尽向好花蹊。
风光无限何兴叹?
耿耿杯殇洒楚泥。
又到清明
文 | 王凤华
天上的阴云
混合着潮湿的思念
在为清明酿一场雨
为团聚酝一场重逢
深埋的思念伴着花开破土而出
那些盛开着的花
红,那么扎眼
白,那么让人心疼
思念和这个季节一起疯长
长势比花木还要凶猛
每一行绿柳每一树繁花
都把我的孤独加重
夹着冷雨的风撕开伤痛的一角
暴露出我鼓胀的思念
风,掂出思念的重量
雨,尝出泪水的咸度
娘亲
托付春风擦干我的泪水
托付清明稀释我的悲伤
托付百花明媚我的心情
风摇落了梨花
就像吹散了娘的白发
清明,是上苍派来俯瞰人间的眼睛
走进清明,走近娘亲
站在清明,我虔诚地向苍天问来生
来生,一定要与娘亲重逢
清 明
文 | 蔺永杰
今天,三界共颤一条弦
悠悠着思念
一蓝子旧时光
刺破眸的泪腺
流淌,梦里梦外的画面
此刻,麦陇拔节
倾诉根的方言
拥簇的姿势
多像老屋子的臂弯
今天,我不在地上
你也不在土下
徐徐青烟
把阴阳串联的梦
送至雨的前端
此刻,风在摇它的叶子
草在结它的种子
而清明,抑或岁月
就盘旋在
风与草之间
清 明
文 | 张洪崑
节日,被安置端庄和严肃的气氛
喧嚣被摒弃,世界安静些许
安静是世界的另一面
烟火袅袅,把搁浅的悲伤摆渡
清净、明亮的花朵
被赋予思念的哀愁
清明,阴雨或天晴
无从左右
而内心居高不下的
湿度指数,也无从左右
这个春天有点白
文 | 谢洪祥
这个春天有点白
一边开花一边生病
恶魔冒犯的武汉
春天只有一种颜色
一批白衣天使来了
又一批白衣天使来了
直至踏着春天的歌声凯旋
这个春天有点白
像雪
盛开在掌心
春 回
文 | 史小满
东风渐次柔,
醉意上枝头。
才问开花未,
芳菲已满眸。
耿金水诗二首
一
祭清明(新韵)
黄昏近处祭清明,
故土难离扫墓茔,
袅袅青烟悲切切,
又闻祖父唤吾名。
二
清明(新韵)
相思万里祭清明,
袅袅青烟上太空,
两界阴阳天色好,
氤氲散尽也无风。
老爷爷
文 | 孙林凤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清明将至,我想起我的老爷爷。
老爷爷是1976年去世,那年,他76岁,我13岁。
在我记忆里,老爷爷一年四季穿着家做的布袜子,绑着腿,黑色下衣,夏天是白粗布中长式褂子,春秋外套黑色夹袄,冬天黑色棉袄。一年四季,老爷爷的衣服总有一层白领子。老爷爷不抽烟,不打牌,就爱干活。
老爷爷对家庭的规矩比较多。我们一大家子人没分家,在一个桌上吃饭,小孩子都是言听计从。吃饭时不随便乱讲话,当然正常的可以讲的。在那艰苦的年代,虽然没什么好吃的,但吃饭时,用青花瓷盘子三四个,整整齐齐地放着咸菜。孩子吃干粮不允随便剩块块,喝饭喝汤不允剩碗底。
现在想来,那时每天就像“坐饭店”,虽有被约束,但总感觉那么清净、那么文明、那么上“档次”。
老爷爷是我们老家那块远近出了名的种地名人,那些走街串巷的,走到某块地,一眼能认出那块是孙玉荀(我老爷爷名)家的。老爷爷种地,那是十分讲究的,“八面见线”,株距行距绝对的统一。可能是因布局合理的原因吧,每年老爷爷种的庄稼收成都挺好。老爷爷还懂土坯房屋的活,经常为建新房人家设计檩梁。简单的木工活、瓦工活,老爷爷也都会。
老爷爷不但会做外面的活,家里的活也做得特别板正。老爷爷拿手的起码有三样:纳鞋底,用夹板子纳鞋底,针距大小一致,行距宽窄相同,拐弯抹角处圆滑,那是少有人能做到的水平;订锅盖,老爷爷订的锅盖,选料均匀,针线精密,切割整齐,装订牢靠。老爷爷切锅盖时,将一根串上长绳的针插在锅盖的中间,手牵绳子一边转一边切割锅盖边沿,锅盖切的圆圆的,绝无一丝偏斜,我看比集市上卖的还规正;刨笤帚,老爷爷刨出的笤帚,既好看,又好用。反正,老爷爷做什么像什么,精益求精,从不懈怠。
老爷爷还做的一手好菜。每到过年,老爷爷亲手操作,家人给他打下手。家堂前的贡品,形状各异,颜色不同,摆放讲究,很有新鲜感和庄重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东坡肉、大丸子和衔着绿香菜叶的鸡。东坡肉切的匀称,码放的整齐。衔着绿香菜叶的鸡活灵活现,分明是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我家的大丸子不像别人家的只是个头比小丸子大,更重要的是在于材料,馒头、山药、肉块都切丁,用调料拌匀,放油锅里炸,之后再上蒸锅蒸熟,吃的时候浇汤,那是我家的美味。我小时候走亲串门吃过的大丸子,都没我家的好吃。
老爷爷算术有一种专门的方法。从前卖地瓜,别人用本子计数,老爷爷拿了一块地瓜,用大拇指在上面掐了花道道,别人算完了,老爷爷拿也出数了,一核对,正好。老爷爷凭着勤奋与努力,创造了如此多的“作品”,让后人记住了他。
老爷爷的才智得以发挥,我觉得我奶奶是起了极大作用的。从我记事就没有老奶奶,是我奶奶伺候老爷爷的吃穿。那时,无论家庭生活多么艰难,奶奶总是让老爷爷吃的比家人好一点,家人吃地瓜面窝头,老爷爷吃玉米面窝头。家人吃上玉米面窝头了,老爷爷就吃上了白面馒头。是我奶奶言传身教让这个大家庭和和睦睦。家庭给了老爷爷至高的权利和尊重,老爷爷的“作品”也是家庭成员的配合的结果。
老爷爷一生是勤劳的,老爷爷对家庭贡献是巨大的。老爷爷享受着劳动的快乐,在快乐劳动中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老爷爷去世40多年,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每一个祭祀节日,我们晚辈都从不轻易缺勤。
一个人能否被后人怀念,绝不是凭当初的权威,一个人对前人的怀念,也绝不是被迫的。此刻我想说,祝在天堂的老人们无所牵挂,过得幸福!
清明寄相思
——忆父亲
文 | 罗蒙蒙
今年清明节与往年一样,要去父亲坟前添一把黄土,算来父亲已经离开我20年了。在床头柜的抽屉里至今还保留着与父亲的全家福,母亲总会说,丫头放下吧!我也总是同样地回答,知道了,其实怎么能够放得下。我怕忘记了父亲音容笑貌,我怕忘记了与父亲的点点滴滴,其实母亲又何尝不是一样。
与父亲的记忆永远得停留在了16岁以前,小时候父亲总爱骑着上海永久牌的自行车,把我放在车子前边的横梁上,骑进深深的胡同里。在拐弯处我总是喜欢按响车把上的铃铛,听着叮铃铃的响声,我与父亲笑着穿过巷子,那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深深地巷子里。我总喜欢在放学后写完作业,跑到胡同口等着父亲回家,每每听到自行车的响声我总会开心地跑过去,看看不是父亲,一脸失望,然后再由失望变为开心,我会扎起胳膊跑向父亲,他会用他宽大的臂膀抱起我,然后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颗棒棒糖,一个甜烧饼,或者是插在车把上的一串糖葫芦,塞给我。我也总是先让父亲尝第一口,载着我,哼着歌谣,穿过那深深的巷子。渐渐地我熟悉了父亲自行车叮叮当当的响声,熟悉了清脆的铃铛声,在等待中慢慢长大,这已经成为了我与父亲的约定。可是有一天我从天亮等到了天黑却仍然没能等来父亲的身影,却接到了父亲因为意外去世的噩耗,父亲没能如约而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跑到胡同口,静静的等待着......尽管我再也看不到父亲的身影,听不到熟悉的铃铛声。或许只有这份等待才能渐渐抚平失去父亲的伤痛。
父亲去世后的第七年,母亲打来电话说平房要拆迁了,让我回家收拾收拾。我又走进深深的胡同,摸着每一块红砖,回忆着与父亲的点点滴滴,欢声笑语,望着深深的巷子,站在曾经等待父亲的胡同口,走进深深的巷子,一眼望去却已经是物是人非。当那轰隆隆的推土机推倒每一块红砖墙,笨重的挖掘机挖起每一块土地,深深的胡同变成一片废墟,曾经的岁月,往事都已不复存在,只留下在深深的回忆里。如今这里高楼拔起,我们也已经搬进了回迁楼里,曾经的美好都已经停留在了想念里。
思念断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思念犹如一杯气味浓郁的烈酒越品越浓,记忆也会越深;思念犹如一杯气味清淳的绿茶,回味无穷,抹不掉深深想念;思念更犹如一杯加了糖的甜水,甘甜入心,却又带着一丝苦涩。
微风习习,春暖花开,愿这温暖的春风带去我对父亲无限的思念和深深的哀思,愿天堂里的父亲一切安好!
怀念母亲
文 | 张居明
日月轮回,斗转星移。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乡村阡陌上的行人,或三两个,或一队队,多低头不语,脚步匆匆,那都是漂泊的游子赶来故乡清明祭扫,为故去的亲人上坟。
茫茫旷野上,子规声声,像是对亲人的呼唤。墓碑前焚烧的冥币化作黑色蝴蝶,翩翩起飞,朝着故去亲人所在天堂飘去。空中不时掠过丝丝细雨,莫非是后辈思念亲人而落下的点点泪滴?
不知不觉中,我那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母亲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闪现,每件事都那样刻骨铭心使我终生难忘。
母亲出生于解放前,14岁就嫁到我们张家,一辈子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妹兄弟五个养育成人。她的一生太不容易了,每每想起这些我便泪流满面。
父亲四岁丧父,七岁丧母,一个人孤苦伶仃和四个姐姐们吃尽了万般苦,受尽了千般罪,寄人篱下的日子实在难熬,后来长大娶了我娘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因为父亲从小和姑父学会了吹唢呐、大管儿手艺,经常上差不回家,我母亲那时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孤单一人在三间土屋里是何等的担惊受怕啊!漫漫长夜,狂风呼啸,有时半夜木门被风刮得叮当作响,似贼人推门,更令年幼的母亲惊恐不已。好在我家过道儿里有一帮和和母亲同龄的姐妹,爱凑到我娘这里玩,父亲不在时,她们就睡在我家和母亲作伴,这样才减少了母亲很多孤寂和恐惧。
后来我们姐妹兄弟相继降生,她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日夜旋转。白天去生产队里下地挣工分,晚上回家为我们做饭浆洗,喂猪喂鸡。那时的冬夜特别寒冷,农村也没有电,每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昏黄的煤油灯下,往往会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如果有嘤嘤的纺车声传来,那是母亲在纺线无疑了;如果在低头穿针引线,那是母亲在缝补衣服,或者纳鞋底,给我们做鞋子。等再一次醒来,有时看到她还在一针一线地忙碌着,甚至赶制到天亮,为的是让我们第二天能穿上新鞋子。在漫长的艰苦的日子里,母亲没能睡过一个囫囵觉。
母亲不但勤劳善良,而且还是个很要强的人,干什么活从不落在人后。当年,生下我第三天就去生产队和小青年推粪(生产队的圈肥)去了,把我交给院中一个老嫂子(比我母亲年龄大)看管,一直到四五岁能跟着姐姐为止。
农村过麦秋是一年当中最累的时候。当时乡间流传着四大累,其中就有拔麦子。“修河筑堤,拔麦子脱坯。”一到芒种时节,全家男女老少齐出动,半夜三更就去地里拔麦子。拔麦子这个活儿,不但累而且脏,还得一直弓着腰,人们往往累得腰酸腿疼,干活时纷纷扬扬的粉尘还会被大量吸入嘴和鼻子里,擤一把鼻涕,吐一口痰,都是黑乎乎脏兮兮的。
中午回家后,我们往往累得连鞋都懒得脱倒在炕上呼呼大睡,而母亲歇一会儿就艰难爬起来为我们做饭。母亲手脚麻利,干什么活儿都快,而且做出的饭菜是有滋有味,现在妻子还经常提起。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困难时期,是她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生活的温馨。
母亲经常说,别人有两只手,咱也有两只手,干什么事凭什么落在别人后头?由于她干活从不耍奸偷懒,为人实诚,生产队里的婶子大娘都愿意跟她结对干活。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她和几个人承包了生产队里的一块棉花地,她们不怕苦,不怕累,日夜长在棉田里,像伺候婴儿一样,为棉花打杈、除草、打药,秋后获得了大丰收,拿回家一摞厚厚的票子,那高兴劲儿就像得了一个儿子!
父亲一生秉性耿直,有难事从不愿向别人张口,里里外外事情全落在母亲肩上。像农村串借牲口耕地播种,互相使用农具家什等,都是母亲亲自跑腿解决。
“儿是娘的心头肉”这句话一点也不假。那是1979年,我写下血书,从济南部队奔赴云南金平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那30多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里,母亲一直牵肠挂肚,尤其是夜深人静时,每每透过窗户,遥望南天苍穹,期望我平安归来。就这样,天天为我忧心的母亲,忽一日满头青丝成白发,像落了一层雪花。
清晨的农村寂静安详,首先唤醒人们的是高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那段特别时期,经常播放李双江那激昂、高亢的《再见吧妈妈》这首歌。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每当这时,母亲眼中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她的视线,直到我回国,把胜利喜讯寄回家中。
战后我从云南前线返回家乡,母亲和大娘大婶儿们共同为我平安归来上了一个大大的猪头供,这时她布满皱纹的脸上像绽开的花朵一样灿烂。
退伍返乡后,我在县城工作,每到节假日便携妻带子回家与父母团聚,母亲总是早早站立在村口等待着我们。她满头的白发随风飘起,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恰如一棵白杨屹立在村头,构成了一道绝美的靓丽风景。
早年,我和妻子的工资都不高,回家时只能买几斤肉,买点蔬菜,跟父母一起包顿饺子,做锅包子吃。有时母亲看到包的饺子少,怕不够吃,就走到一边让我们吃。她说在家里吃早饭晚不饿,其实她哪里是不饿呀,那是一种深沉的母爱!
2000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只幸福欢乐地生活了三年。因为她血压高,得了半身不遂,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后,就开始在我们姐妹兄弟五个家中轮流伺候。每次从农村老家接到城里我的家中,我都要背着她休息几次才能上到住的楼上,然后给她大清洗。先把她的头洗干净,当看到她满头银发时,我止不住一股股酸楚涌上心头,母亲一生为我们五个子女操劳多么不容易啊。给她洗脚时,搓揉她那只不能动的脚,感到一点动感时,我都会心中暗喜,祈祷上天能让母亲能重新走路呢!
熬过了五年之后,一个应该是最寒冷的日子。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叫化,而那天是那样的阳光和煦,天空没有一丝风,母亲没有留下一句话就静静地走了,就像她的善良慈祥一样。
世上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母亲初七离世,五天后出殡,正是父亲去世之日;母亲得病不能行走之时,正是父亲逝世之日;而他们哺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正好让我们每人伺候一年。
母亲昏迷了七天七夜,水米未进,我一直陪伴在身边未曾离开半步。有时夜晚独自走到院中仰望星空,默默祈祷上天保佑母亲醒来,哪怕用我的生命换回她再陪伴我们几年,但天命难违,母亲在腊月初七那天上午九点,我刚刚转身她就悄悄去了天国。我在想,母亲是怕我们和她面对面阴阳两隔而悲痛欲绝才悄悄离开吗?依照母亲那一贯的善良和爱,我想她应该是这么想的。
今天,你疼爱的儿子和爱你的儿子又来到你的坟前,娘,你在天国还好吗?
德州日报全媒体出品
来源 | 德州市作家协会
编辑 | 李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