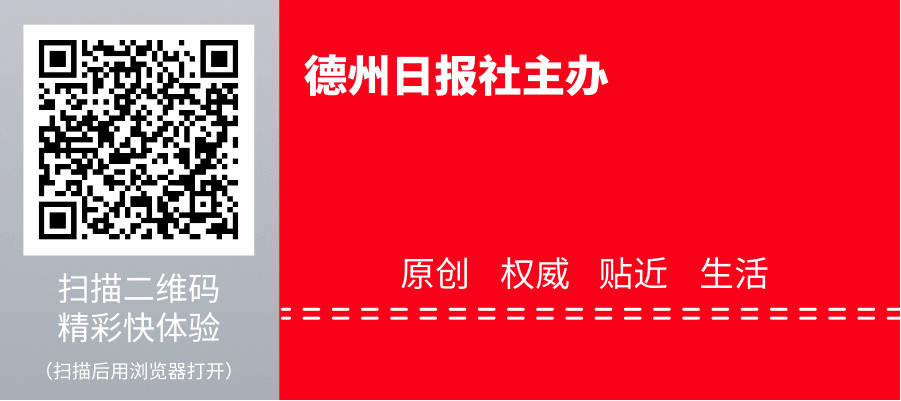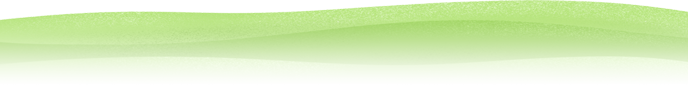

绿树浓荫蝉声长
文|莲 韵
聒噪的蝉声从一片绿荫中传来,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吱吱的长鸣把一个夏天拖得悠长悠长。
“高蝉多远韵,树茂有余音”,炎炎夏日,骄阳似火,那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给人们带来了一份清凉。绿是大自然的衣衫,是希望,是生长,夏天最喜欢的是那一抹绿,而蝉声又是和夏连在一起的,蝉躲在浓浓的绿荫里,吸取甘露,临风高歌。蝉鸣的最热烈的时候,也是整个夏季最酷热的时候。
在我的家乡,一到了芒种,蝉便出现的了。先是试探性的一声、两声,这个时候出现的是一种幼小的蝉,背部和翅膀上有棕褐色的花纹,和树干颜色一样,所以很难以看到它。黄昏时候从泥土里爬出来,不过它不一定非要攀上大树,那些低矮的花草,或者是一个枯枝、小树也许就是它的栖息之处。爬的将离开地面就停在那里等待蜕变。这种小蝉的叫声很单一,又尖又细,像一根细细的长丝线,软弱无力,仿佛一拽就断。
我们所说的蝉,一般是指那种大而黑的蝉。要等七月份才出现,这种蝉一叫,蝉的季节才真正到来。它的叫声嘹亮,肉质鲜美,所以是人们扑捉的对象。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的傍晚,我们每人拿一个罐头瓶子,或者捎上一根竹竿,早早地来到湾边那片浓密的树林里去找蝉狗。
蝉狗的出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时候尚早的话,蝉狗还躲在洞里,它会用前爪小心翼翼地将洞口先掏开一个小眼,自己藏在泥土里,伺机便破土而出。有的正在树干上爬,一下子就能逮住了,有的则爬到高树枝上,便借着朦胧的夜色辨别出来,用竹竿扒拉下来。
最有趣的是蝉的蜕变,它先用那锯齿一样的爪子牢牢地在树皮上一抓,然后一动不动地慢慢积蓄力量。全身深棕色的硬壳,先是从背部出现一道裂痕,嫩绿的脊背渐渐拱起来,身体不停地抖动,显然是很痛苦的样子。终于它露出了头部,抽出潮湿的皱巴巴的翅膀和腹部的足,最后只剩下尾部还在壳内,这时候它会来一个惊艳的动作,腾空一跃,瞬间整个身体倒立。这样挂在风中半天,它的翅膀渐渐舒展,身体慢慢变黑,便抖一抖翅膀,“吱”地急叫一声极快的飞向绿荫中了,留下一个空壳在树上。小时候曾经帮蝉脱去硬壳,结果蝉的翅膀却再也伸展不开了,很快奄奄一息。大概痛苦只有自己承担,才能完成蜕变,而别人是无法越俎代庖的吧。
据记载,蝉的一生都依附于树木。幼虫时,隐于地下便靠吸取树根的汁液生存。在长达几年漫长的幽居时光里,没有光明,只有黑暗,没有繁芜,只有孤独。在潮湿的泥土里自己拥抱自己,等待破土而出,等待生命的裂变,等待光明的到来。因此,蝉的生命只属于一季夏,在短短几周的生命里,它极力地歌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那一声声嘶鸣,都是对美好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对自由的呐喊,对生命的渴望!
夏天的午后,烈日当空,蝉在湾边以及人家房前屋后的柳树、榆树、杨树和枣树、梨树上歌唱,是蝉鸣更热烈更旺盛的时候。那叫声,时急时缓,或长或短,一时成了夏季的主旋律,它们的交响乐成了人们午休的催眠曲,“吱——吱”的编织成一帘细密的清梦,萦绕在耳畔。整个夏天,那蝉鸣就不曾间断。很多时候人们竟忘了它的鸣叫,实在是因为这种声音和夏天与生俱来的,只要有夏天,就有绿荫,有绿荫就有蝉鸣。
而对于从不睡午觉的孩子们,浓浓的绿荫却成了我们的快乐园。粘知了,找蝉蜕,知了可以给贪吃的鸡鸭改善伙食。至于那些蝉蜕可是我们的宝贝,因为它是一种药材,供销社要收购,虽然卖不了几个钱,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却诱惑着我们小小的心,满满一袋子蝉蜕换来几毛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整整一个夏天,我们在快乐地玩耍,蝉在使劲的歌唱。它们是为生命而歌,为明媚而歌,为快乐而歌,把最美的旋律和最深的眷恋,都献给了夏天,献给了养育它们的那片绿荫。
“吱——吱”,窗外蝉声又起,绿影婆娑,清凉的夏风,把那些美丽而温馨的记忆吹的渐渐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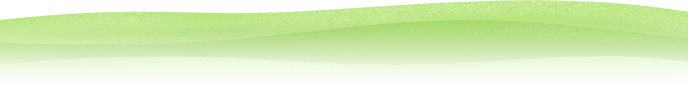

清晨的笛音
文|康红敏
清晨,我骑车去上班,一出小区大门,便汇入人来车往的上班洪流之中。路过银座广场的时候,忽然一阵清脆的竹笛声传入耳畔,声音断断续续,并不流畅,显然是个新手。但是却清脆悠扬,在这熙熙攘攘的清晨,如一股清泉流进心田。
我循着声音寻觅,广场那边是一群漂亮姐姐在跳广场舞,北面路边的台阶上三五成群地站着各色的人,有晨练的、有休闲的、有等待公交上班的,还有穿着橘黄色马甲的环卫工人。忽然,在人群中我发现了一位大叔,他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车棚是简易的帆布搭成的,车箱里放着一把大扫帚,上面扎满了红的黄的布条,我知道,这样扫帚更密实,清扫起来更便捷。大叔坐在三轮车的驾驶座上,灰体恤外面套一件橘黄色环卫服,一根竹笛横在嘴边,饱经风霜的手指随着节律轻轻地上下移动着,于是,那清脆的笛音又飞出了竹笛:“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他神情那样专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我不禁看呆了,以至于绿灯亮了都没有察觉。驶过马路时,耳边充斥着不绝于耳的汽笛声,可心里却还是荡漾着那阵阵清脆的短笛音。它像一股清冽的甘泉,缓缓流淌,轻轻拂去心里的忧伤和疲倦;更像一阵夏日的清风,为你注入一股欢快的能量。
于是,每天清晨,我都尽量早些出门,为了能在那个十字路口,听到老人的笛音。每每路过十字路口,都能看到大叔坐在他的三轮车里,短笛在口,手指轻移,眉头紧锁,专注在音乐的王国里。那些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曲子一首首地飞出,那些又何尝不是陪伴他从青春年少一路走来的光阴呢?
有一天我动身晚了,走到银座广场这个地方,竟没有听到笛音,也没有看到老人。我的目光四处寻觅,也不曾看到那个身影。刚刚下过雨,路面还很湿,等车、晨练的人们也少了很多,我怅然若失,随着绿灯驶过了路口。
忽然,在不远的前方,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位老人,穿着橘黄色的环卫工作服,拿着扫帚,正在路边的国槐下,一下紧一下的扫着树上飘落的黄花。“翠凤毛翎扎帚叉,闲踏天门扫落花”,那细碎的花瓣,像撒了一地的碎金,老人轻轻地扫起它们,神情是那样的认真,他并不曾留意到,有一个过路的行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他也不曾想到,他的笛音,给了那些过路的行人多少抚慰与力量。
这是一位多么值得尊敬的老人啊!他披星戴月,勤勤恳恳,余热生辉,默默奉献!用他一双粗糙的手,描绘小城美丽风景。他累并快乐着,他的笛声美,心灵更美!霞光普照,晨辉润染。脚下的单车,似乎顷刻间轻便了许多。我骑车渐渐远离了老人,踏着朝阳,奔向自己的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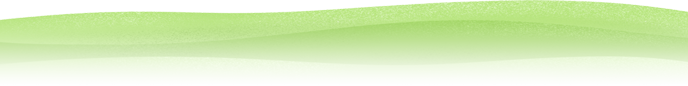

家乡的火车站
文|段兴君
我工作生活在A城,父母居住在D城乡下,距离火车站30公里。从A城到D城,火车成了我的主要交通工具。
多年来,我已形成习惯,无论是经意回家,还是每每路过,只要到了家乡的火车站,就要往家里去个电话,有时候还顺便到家看看,短时半天,长则竟日。早些年,到站下了火车,到市里朋友或同学那里找个自行车,骑车回去,后来交通便利了,干脆打个出租车。父母日渐年迈,回家和进出家乡火车站的次数也多了起来。父亲离世后,我曾把母亲接过来住,但生活了一段时间,母亲还是执意地要回乡下老家去,母亲说:“城里生活不习惯,不如在家方便,烦闷时找邻里老姐妺们拉拉呱,觉得心里踏实”。母亲回去后,相互间的牵挂更加强烈。每次回家,离车站还有一段距离,我就把电话给母亲打过去,母亲知道我来,不管严寒还是酷暑,早早的就等候在村口了。见人,就说“儿子回来了”!不管人家问与不问,高兴地像个孩子。见了我,一边上上下下的打量,一边疼爱的说这次黑了,那次瘦了;一会又说起西邻周家的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东邻的王家添了个胖小子。不管你听与不听,认识不认识,说个不停。到了家,第一件事又是爬到炕上打开炕橱,但一次比一次吃力。取出她珍藏的包裹,里三层外三层的,小心翼翼的打开。有时是柿子,有时是石榴,有时是母亲认为最好的东西。母亲看着己经菌化的柿子,不断地自责,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看着已经干瘪的石榴,我只好从母亲的手里接过来,艰难的扒开放到嘴里几粒,母亲见我咀嚼的样子,好像自己也在享用,瘦干的脸上笑开了花。我劝母亲说:“现在买什么都方便,以后不要存放了,自己用吧”,母亲却坚持说:“这是咱自家院里出的,吃着放心”。临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母亲总是拾掇一大堆,似乎还意犹未尽。
然而,这次出差,离家乡的火车站越来越近了,我却不知所措,几次拿起手机,几次又都放下,母亲离世已经半年多了,这次的电话我该打给谁呢?多少年来,家乡的火车站不知给我带来了多少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此回家!但这一次却使我心痛。每每在此回家,这次我该去哪里呢?家!近在咫尺,忽然间却变得是那样的茫然和遥远了!惆怅中,车到站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鬼差神使的跟着下车的旅客下了车,傻傻地望着家的方向立在了站台,但又不得不怅然的跟在上车旅客的后边再次上车,呆呆地坐在位上。此时的我,像是海上的浮萍,飘得有些不安;又像是断了线的风筝,第一次感到是那样的无助!嘟!嘟!嘟!车门关闭了,列车离站,家乡在我面前已是模糊一片!
德州日报全媒体出品
来源 | 德州市作家协会 编辑 | 李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