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 电 影
□ 李慧善
一天,我突然收到初中同学发来的一组照片,他说受县文化站派遣,正在我村义务放电影。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人物,瞬间勾起我儿时看露天电影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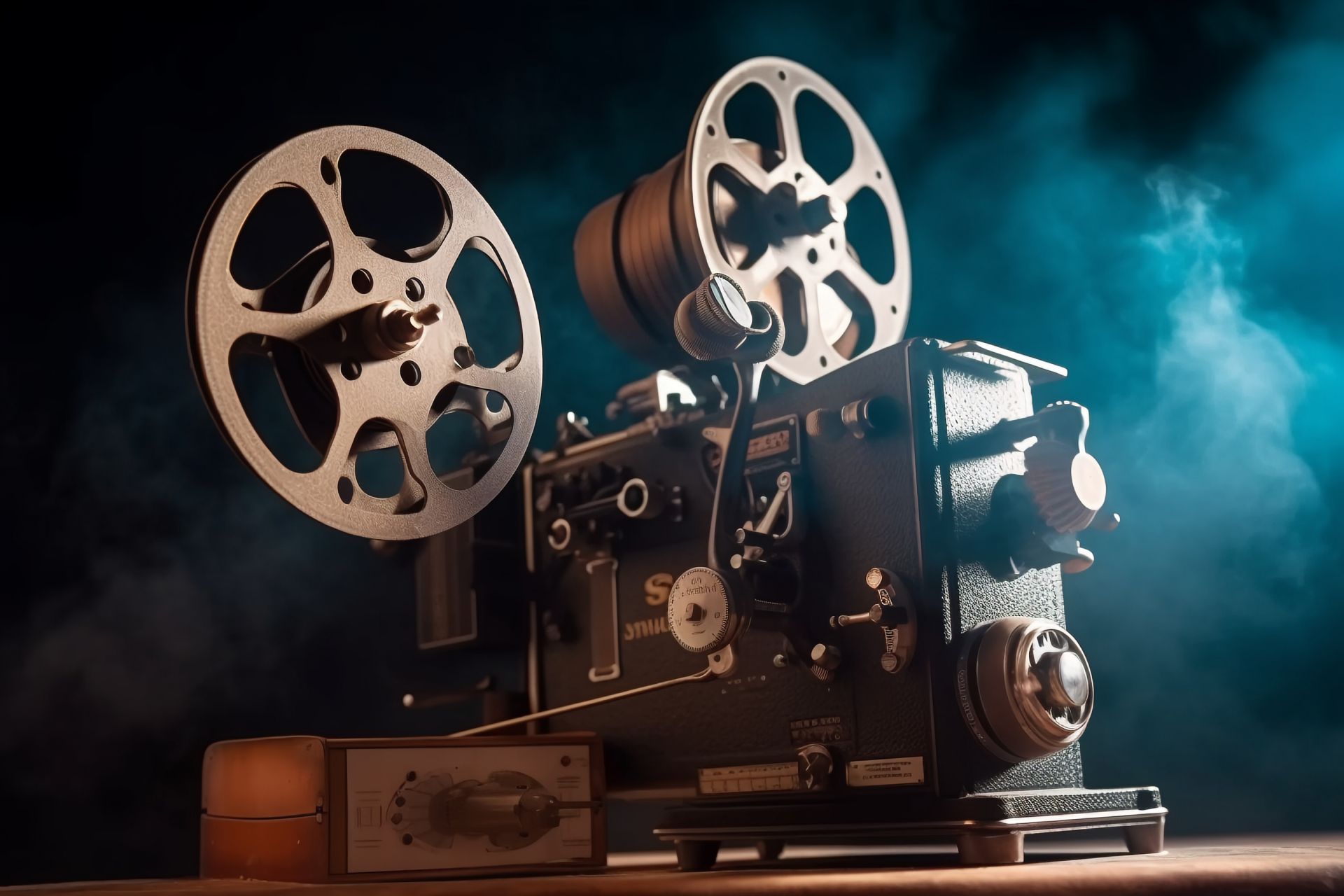
小时候,娱乐设施十分单一,看电影便成了我们最大的期盼。记得一个夏日傍晚,村口老槐树上的大喇叭骤然响起:“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晚七点大队部放电影《小兵张嘎》……” 这声音恰似一粒火种,刹那间点燃了整个村庄。
孩子们是最先沸腾起来的。正在河边摸鱼的光屁股小子们,连裤衩都来不及穿好,湿漉漉地拎着塑料凉鞋就往村里狂奔。放牛娃随手把缰绳往老黄牛脖子上一绕,任其一摇一摆地回村——笃定老黄牛认得回家的路。女孩子们相互帮忙编辫子,有个心急的扯断了红头绳,干脆咬在嘴里继续忙活。甚至不知谁家灶膛里的红薯还没烤熟,小主人就已没了踪影。
大队部门前的麦场上,两根毛竹支起的白色幕布,宛如一面神秘的旗帜。我们这些 “先遣部队” 早早搬来砖头占位,最前排的 “VIP 座位” 永远留给五保户李大爷 —— 他是全村唯一与日本鬼子拼刺刀致残的军人。狗剩不知从哪儿弄来半截粉笔,在幕布背面画乌龟,被村干部揪着耳朵拎走时,幕布上晃动的影子好似一出活灵活现的皮影戏。
天渐渐暗了下来,家禽家畜都归了圈,连平日里爱叫的狗也安静了。眼见大人们陆陆续续赶来,放映员取出片子,架在机器上,一束光瞬间投射在幕布上。在光束里跑跑跳跳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幕布上被放大,兴奋地做出各种动作,用手比画着不同形状,调皮极了。
被大人招呼到座位上的孩子也没闲着。身上的汗在大人轻摇的蒲扇下慢慢消退,可没过几分钟,一看到 “八一电影制片厂” 几个字,便又欢呼雀跃起来——是战斗片。当放映机开始转动,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 这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奢侈的精神盛宴。《地道战》《地雷战》中英雄们智斗敌人的情节,让观众们不自觉攥紧拳头。
中场换片的十分钟最为热闹。半大小子们歪戴着草帽,模仿嘎子堵烟囱的经典镜头;姑娘们热烈讨论着《小花》里刘晓庆的麻花辫;会计家的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与远处田埂上手电筒的光点遥相呼应。
放映员通常先放《植树造林》这类培训影片,再播放《少林小子》等武打片,这般安排自有考量。他担心一开始放动作片,孩子们过于兴奋,容易发生摔伤、碰伤等意外。等一部电影放映结束,孩子们的兴奋劲儿褪去,也有了些困意,这时再放动作片,现场就会安静许多。
露天电影院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情感共鸣的所在。散场后,人们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埂上,年轻姑娘们悄悄讨论着《甜蜜的事业》中的恋爱观;大人们观看《天云山传奇》时,会陷入对 “历史的反思”;《庐山恋》中张瑜那个惊鸿一瞥的 “新中国第一吻”,成了解放思想的标志;《瞧这一家子》中陈强父子闹出的笑话,让大家意识到幽默不再需要小心翼翼;而《芙蓉镇》里姜文扫街的长镜头,又让多少观众在黑暗中默默流泪。这些影像如同社会情绪的晴雨表,折射出人们情绪的微妙转变。人们争论着剧情,手中的电筒光划破夜空,好似流动的星河。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大家手头宽裕起来,黑白电视机逐渐增多,有的家庭还添置了彩电。电视节目新颖丰富,吸引力越来越大,村里再放电影时,来看的人少了许多。接着 VCD 和 DVD 出现,人们买来光盘在家播放,吹着电风扇,舒适惬意。于是,很少有人再去村子大街上看电影了。
21世纪初,随着电脑普及和网络技术发展,人们观看影像更加便捷,内容也更加丰富,想看什么、何时看、看多长时间都随心所欲,还能随时回放。自20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电影事业飞速发展,走进影院观影不再奢侈,一年看几场新片已是平常事。农村的流动电影放映队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如今,人们想看电影,可以去电影院,也能在家用投影设备观看。近几年,一些休闲娱乐场所特意开设了充满怀旧氛围的露天电影场地,供爱好者们体验。只是,这些都找不回小时候看露天电影时的那份兴致了。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