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影旧梦处 德州忆影长
—— 人民电影院的岁月回响
□谭晓红
小时候的夏天,蝉鸣在枝头不知疲倦地喧嚣,宛如一曲永不落幕的乐章,为那段纯真岁月铺展生动的背景音。父亲宽厚有力的大手,紧紧攥着电影票,引领我们兄妹缓缓穿过马市街熙攘的人流——叫卖声、谈笑声在耳畔此起彼伏,织成一幅鲜活的市井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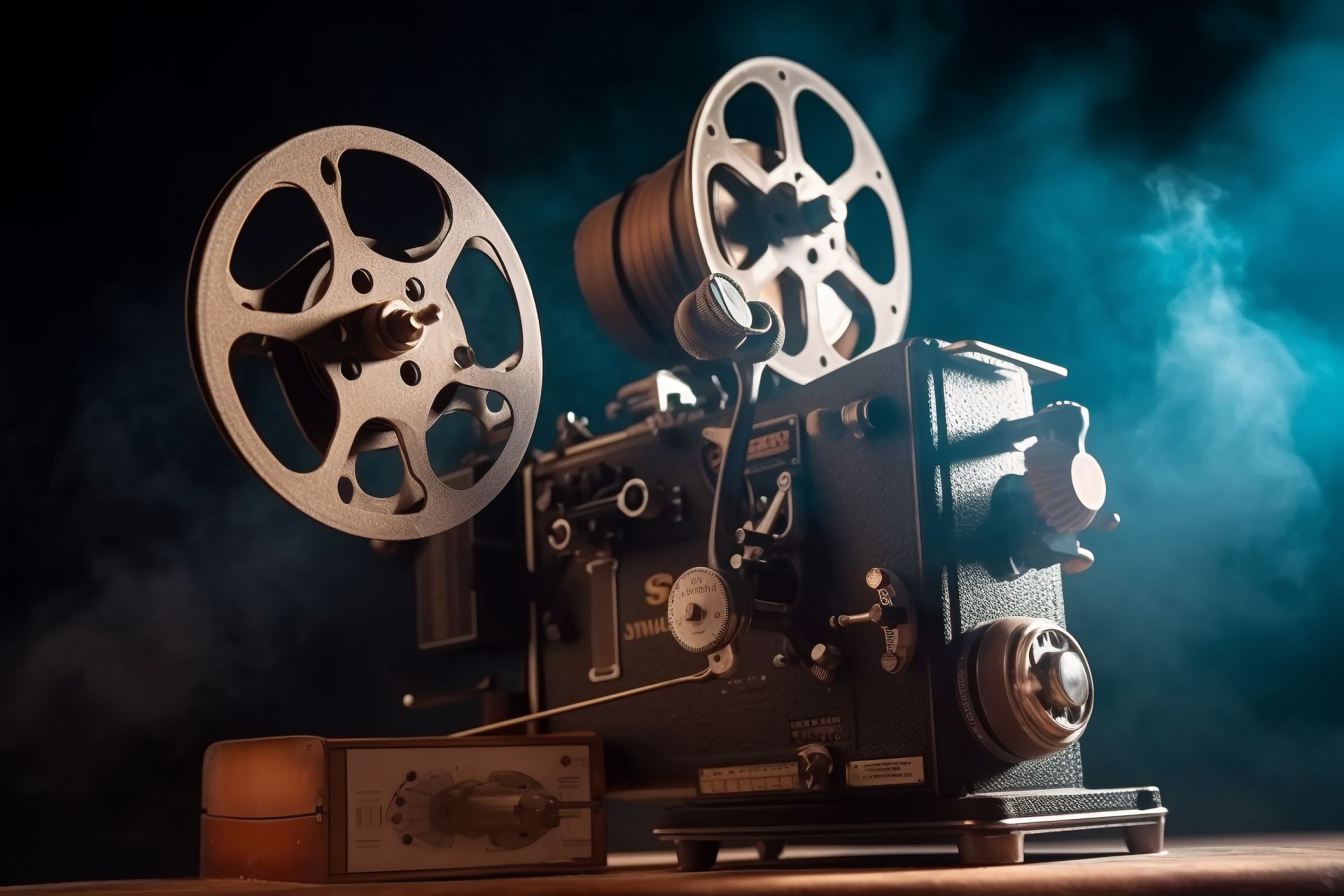
到了人民电影院前,父亲轻轻掀开厚重的门帘,一股混合着木头潮气与淡淡烟味的凉气扑面而来,与外面的燥热撞个满怀。映入眼帘的,是那一排排深棕色的连排硬木座椅,宛如忠诚的卫士,静静守护着这里的每一段光影记忆。椅面早被磨出温润的油亮,像封存着无数人的体温,沉睡着一段段磨不去的回忆。前排座位底下还沾着没清理干净的瓜子壳,踩上去吱吱作响。座椅之间的过道并不宽敞,人多的时候,大家得侧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影院的天花板上,几盏昏黄的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墙壁上张贴着各种电影海报,虽然有些已经微微泛黄,但依旧难掩其艺术魅力。
父亲熟门熟路地走向中间过道,手指在椅背上轻轻一叩:“就这儿。”他说着从布兜里掏出油纸包,馒头的热气透过纸缝钻出来,混着冰棒纸“刺啦”撕开的脆响——红果味的冰棒裹着一层薄霜,咬下去先尝到冰碴的凉,再是果子的酸;奶油的则是绵密的甜,化在舌尖能抿出淡淡的奶膻气。我们小口舔着冰棒,看阳光透过高窗上的玻璃,在对面墙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像谁在悄悄眨眼睛。
这座立在商业街东口的影院,藏着曲折的过往。1933年建的“移风社”是它的前身,那时专演京剧,咿呀唱腔裹着华丽戏服,木质舞台的地板踩上去“吱呀”晃,戏班的武生翻筋斗时,台下嗑瓜子的声响能盖过锣鼓点。1939年改成“德光剧场”后,日本人用石灰水刷白了雕花的木梁,却遮不住梁柱深处浸着的桐油香。1949年冬天,解放军战士用铁锹铲掉墙上的日文标语,新钉的木牌上“人民电影院”五个红漆字,在雪光里亮得耀眼。1958年迁到现址后,褪色的幕布、坚实的砖墙里,早已悄悄嵌进几代人的悲欢,见证着城市的起落,也收纳着德州人在光影里的笑与泪。
它像一扇瑰丽的窗,让我们既能撞见国内佳作的锋芒,也能瞥见外国影片的风情。那个年代的浪漫里,热恋的情侣总爱牵手走进影院——两毛钱一张的票,配一瓶冒泡的汽水,就能在光影里泡上一整个午后。幸福像夏日掠过心头的风,清爽得不带一丝杂质。
国产影片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我们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八十年代的银幕格外热闹。《高山下的花环》放映时,影院里安静得只能听见胶片转动的声音。当看到硝烟漫过战士坚毅的脸,梁三喜的母亲数着账单上的“欠620元”时,坐在我旁边的老太太突然抽噎出声,手里的蒲扇“啪嗒”掉在地上。不少观众忍不住啜泣,有人甚至用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演到《牧马人》里许灵均和李秀芝在草原上盖土坯房,银幕外不知谁叹了句“这才是过日子”,惊得前排打瞌睡的大叔猛地抬起头。放映结束后,观众们还沉浸在剧情中,不舍离去,小声地讨论着许灵均与秀芝质朴的爱情。《庐山恋》里的庐山云雾缠着纯真的爱恋,银幕亮着,观众眼里也亮着对美好的向往;看着男女主角在庐山的美景中漫步,后排传来“啧啧”的赞叹。我偷偷扭头,看见穿的确良衬衫的小伙子正往姑娘手里塞水果糖。
而与此同时,外国影片也如一阵别样的清风,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盛宴,同样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卖花姑娘》的悲戚里藏着不屈,看时总有人悄悄抹泪。电影里卖花姑娘一家的悲惨遭遇深深触动着观众的心,一位老奶奶边看边用手帕擦拭眼泪,嘴里还念叨着:“太可怜了,孩子太可怜了。”我也早已成了泪人。《追捕》的紧张剧情攥着人心,高仓健的冷峻成了多少人心中的剪影;影片中精彩的追逐场面让观众们心跳加速,大家都紧紧盯着银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流浪者》的《拉兹之歌》一响起,影院里总有人跟着轻轻哼“阿巴拉古”,像被异域的风拂过;一些年轻人甚至跟着节奏轻轻摆动身体。
这些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成长的养分。学校组织看《小兵张嘎》时,我们背着帆布书包排着队进场,谁的铅笔盒没盖紧,“哗啦”掉出一捧彩色玻璃弹珠。银幕上嘎子用枣核射伪军,台下的我们攥着拳头直使劲;前排的同学突然高喊了句“打死他”,被老师轻轻敲了下后脑勺。看完《闪闪的红星》,大家的作业本上写满了“向潘冬子学习”,钢笔水洇透了纸背,像映着一片小小的红霞。
德州人民影院的光影里,除了那些熟稔的经典,总有些影片带着特别的印记,沉在时光深处。
《沂蒙颂》便是其一。银幕亮起,沂蒙山影在光里舒展,山风卷着故事漫过来。红嫂用乳汁救伤员的瞬间,影院骤然静了,连咳嗽都轻成了耳语。黑暗中,无数目光凝着那朴素身影,看战火里那份比山还沉的情谊——恍惚间像站在滚烫的山坡上,听粗瓷碗碰出声响,听“生死与共”在风里反复冲撞。那不是故事,是能触到的温度,一条线牵着银幕内外;散场时,红嫂的身影早和这片土地的记忆缠在了一起。
《洪湖赤卫队》也如此。洪湖浪一漾,韩英的歌声就顺着水纹淌出来,清越里裹着硬气。“洪湖水呀浪打浪”响起时,影院像漫了水汽,有人跟着哼,调子歪歪扭扭,心却热得发烫。看赤卫队员驾船闯芦苇荡,暗处似有无数拳头攥紧;听韩英狱中那句“砍头只当风吹帽”,周遭呼吸都沉了,像有团火在胸腔里燃烧。那水是赤子血脉,那歌是护家的誓言。散场夜风里,浪涛声、挺括的脊梁总在眼前晃——红嫂的柔,韩英的硬,都带着泥土江河的重量,在记忆里,久久落不了幕。
物资不丰的年月,看电影是顶大的福利。海报一贴,小黑板写上片名,售票窗前就排起长龙。小小的票根,红的绿的,攥在手心像捧着稀世的宝贝。没有电子游戏和智能手机的童年,银幕的光就是夏夜最亮的星,照亮了简单的快乐。售票窗口前,人们排起长长队伍,翘首以盼,互相交流着对即将观看电影的热切期待和对未知故事的好奇。
时代推着数字影院冒出来,老影院渐渐成了背影。那曾经承载着无数欢声笑语与青春梦想的人民电影院,虽已在时代浪潮中逐渐远去,但其所代表的纯真与温暖,却如同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亮着我们人生的漫漫长路,给我们心灵深处带来永恒的慰藉,让我们在前行的旅途中,始终能回望那段熠熠生辉的岁月。
在老德州人心里,人民电影院永远占着一块地。这份记忆,不仅是对青春岁月的深情缅怀,更是对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纯粹情感、对生活质朴热爱的坚守。人民影院就像时代的见证者,它的变迁映射着社会的进步;而那些珍藏在心底的回忆,如同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在新时代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坚定地追寻梦想,续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

作者简介:谭晓红,女,德州市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作家《诗刊》子曰诗社社员,山东省诗词学会会员,德州市诗词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华辞赋》《历山诗刊》《诗坛》《五色土》《德州诗词协会》等。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