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砺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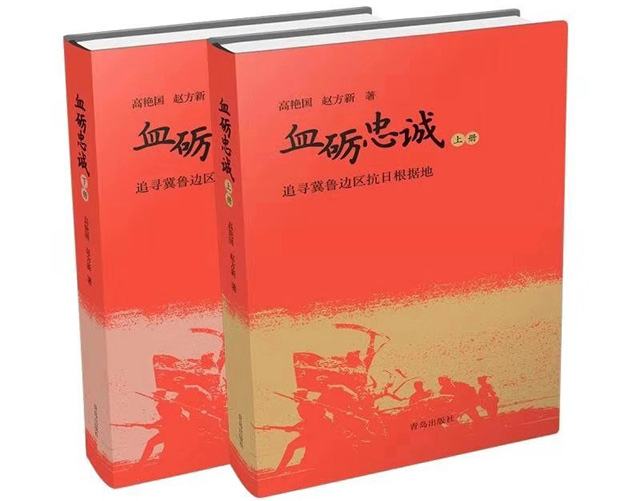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以无限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们!
第二章 冀鲁边前传
悲怆马颊河①
1925年早春时节,一辆毛驴车吱嘎吱嘎地行驶在乡间盘曲的小路上,叮当叮当的铃声随着黑色叫驴一耸一耸的脖子,送往岑寂的旷野。
车上一个农家子弟打扮的青年人不住地回头张望着朝暾笼罩的龙王庙村,那扭着腰身升起的炊烟是他再也熟悉不过的景象了。他循着这升高的炊烟往下想象,便似乎看到了正蹲在灶膛前俯身填柴的母亲,她的面庞被灶火映红,皱纹如波浪般围绕着那双浑浊的眼睛荡漾,还有她那双粗糙的手掌抚过他脸颊的生疼感,也是他永远忘不掉的一种慈爱,而现在这双手正窸窸窣窣地聚拢了柴草,一把把喂进灶肚……他的鼻腔即刻被酸涩的感伤蜇了一下,不过犹如微风过林,树梢的颤动只是一种礼节式的答复而已,投奔广阔的未知世界的兴奋开始消解着心头的离情别绪。是啊,他要走一条祖辈没有走过的路,看看祖辈没看过的大千世界,哦,那个叫天津卫的地方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欢迎自己呢?
胡恒熙从家乡庆云县离开的步伐,携带着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憧憬和豪情:要么被世界接纳,要么创造新的世界。在闭塞的乡村度过童年、少年的胡恒熙,从各种渠道捕捉着外部的讯息,他为五四运动的洪波巨澜而激动,他被一张介绍新文化的小报迷得三魂出窍,他对听闻的军阀混战愤慨异常,他从身边正在发生的细微改变小心翼翼地推测着外面世界的变化,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自己走向远方……
19岁的胡恒熙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泊镇火车站钻进了铁壳子车厢,一路咣当咣当、摇摇晃晃地赶往天津。不久,他成了直隶省甲种水产学校的一名学生。清苦的学生生活对于来自乡间的他不成问题,青春的荷尔蒙在打球跑步中得以释放,而思想的苦闷却找不到适当的宣泄口,他发现学校当局还在推行着“尊孔复礼”的陈旧教育观念,反对学生关心政治、关注时局,对思想活跃分子严防死守,甚至采取革除学籍的做法。胡恒熙悄悄到校外购买各种报刊,了解思想界的最新动态和国内外大事,跟同学们评论时事,鞭挞军阀误国殃民。他经常一人彷徨在深夜的校园里,仰望星空,不知如何处置胸中的一腔热血。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胡恒熙引向了抗争社会不公的革命道路。
有一天,他去同乡刘济安家做客,正说着话的时候,门外有人喊了一声“二哥,我来了”,房门开处,闪进一个身材魁伟、面色白润、梳着背头的青年人,柔和的眼神里饱含着诚挚的笑意。
刘济安招呼道:“三弟快坐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庆云县的胡恒熙,正在天津读水产学校。”他又转头对胡恒熙说:“他是我家老三格平,满脑子的时髦思想,你们拉拉呱吧,说不定能拉到一个路上去。”
胡恒熙早就耳闻过“三少爷”的不少传闻,那时的刘格平在外界看来是个标准的“异端”,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整年在外拎着脑袋飘来飘去,还蹲过军阀的大狱。他直截了当地问刘格平:“三哥,你眼界比我们当学生的都宽,你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刘格平看着这个面色微黑的青年人,颇有些感触,自己不也经历过他正在经历的迷茫和愤懑吗?但萍水相逢,没有任何了解,他不能贸然吐露真话,就反问他:“你说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胡恒熙说:“我出门的时候,家里人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好好读书,说是读了书就可以吃饱穿暖。可是我一人饱暖了,天下老百姓还饥寒着,我心何安?现在的社会军阀横行,兵连祸结,土豪劣绅趁火打劫,民不聊生,真看不到一点光明,谁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呢?”
刘格平抱着茶杯,望着胡恒熙,听他慷慨激昂,隐隐生出了缕缕好感,中国的青年人如果都像眼前的胡恒熙一样善于思考问题、敢于直面现实,那我们的国家何愁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呢?他平静地说:“恒熙你问得好!青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只要我们不被社会腐蚀掉,敢于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光明的未来也就不远了。”
胡恒熙听了既欢欣又焦急地问:“我们该怎么做呢?”
刘格平没有直接回答他,还是避实就虚:“对于现在的社会和将来,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我们青年人要干一番前人没干过的事业。”
胡恒熙眼里射出一种光辉,向刘格平追问道:“我们要干什么呢?”
刘格平只是泛泛地给他谈了当前国内的形势,鼓励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提高思想觉悟。虽然没有得到最想要的答案,胡恒熙还是从刘格平的话语中受到不少启发。而胡恒熙刚毅执着的性格,也给刘格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这次交谈促成了胡恒熙的武汉之行。1926年秋,天津的大街小巷灌满了呼呼的风声,落叶在马路上翻滚,海河泛着粼粼波光,滩涂上的野苇摇晃着白花花的芦花,不知名的水鸟低低掠过水面。胡恒熙健步走进刘格平的寓所。刘格平开门见山地问他,有一个去武汉政治学校学习的机会,不知他感不感兴趣。胡恒熙有点惊讶,但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了。他知道武汉是国共合作的革命中心,早已心向往之,只是关山重重,恨不能达。刘格平告诉他,这次学习是中共顺直省委安排的,为的是培养适应革命形势的军政干部。胡恒熙表示,一定珍惜这次机会,不辜负党的期待。
胡恒熙在武汉的学习很短暂,很快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做宣传工作。
1926年12月,胡恒熙见到了受中共北方区委之命前来武汉国民政府沟通的刘格平,心里乐开了花。
寒暄过后,胡恒熙面露忧色地说:“我有点不明白。”
刘格平问:“有什么问题吗?”
他说:“真奇怪,共产党不是很革命的吗?!为什么还有人在活动反共呢?”
刘格平一愣:“这是哪里的事?”
胡恒熙愤慨地说:“我最近经常碰见有人宣传反共,他们还拉人加入他们的组织。”
刘格平说:“国民党内一直有一股反共的逆流,这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你参加了吗?”
胡恒熙“哼”了一声:“我怎么可能参加那种组织呢?可是你告诉我,到底应该参加什么样的组织才好?”
刘格平略作思考说:“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你如果现在还搞不清参加什么好,不参加也可以,但不要反共,共产党是最革命的。”
胡恒熙说:“没问题!我还是能分清良莠的。”
这次见面很短暂,刘格平身负重任,穿梭于各方,后又乘船去南昌见到了蒋介石,就北伐问题汇报了北方的有关情况。而胡恒熙最终在反共氛围越来越浓的武汉窒息难安,于1927年7月重回天津,跟刘格平见了一面,便被顺直省委派往庆云县工作。其后他在刘格平的介绍下入党,担任盐山、庆云联合县委书记。
在北方,发源于河南省濮阳县澶州坡的马颊河并不是一条重要的河流,虽也忝列《禹贡》“禹疏九河”之一,但比之于江、河、淮、济“古四渎”,那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了。马颊河因河势上广下窄,状如马颊而得名。这条水势平缓、河床狭窄的河流由南而北,像一条柔柔的飘带穿行于华北平原,于山东省无棣县黄瓜岭注入渤海。或许由于它的性情过于温和,因此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较平淡,甚至有些平庸。但1934年春天,这条一贯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河流暴怒了,以一种极度暴烈的方式切入了历史叙事的现场。
春节刚过,节日的氛围依然没有散去,一张张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庆云县政府的布告将人们重新打回了严冬:“奉省令,疏浚庆云县境内三十里长之马颊河道,所需费用就地筹款,每亩加捐一元,限期完成,违抗者严惩不贷。”
老百姓围着布告跳高骂娘:“这是什么鬼主张?还让人活不活?”“我们去挑河,春耕种不上,吃什么?”“国家发下来的挑河费又让哪个王八犊子吞了!”“眼下青黄不接,吃的都没有,哪有力气挑河啊?”……叫苦连天,闻于四野,民怨沸腾,怒火燃遍十里八乡。
马颊河流经山东数百里,只有庆云县南端三十多里的河段在河北省境内。马颊河由于多年失修,河床淤塞,涝不能排,旱不能灌,急需疏浚治理。当时主政山东的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疏浚河道曾给庆云县政府拨款三万元,但贪婪成性的庆云县县长傅奎升一伙却将此款分肥,又搞了一个“就地筹款”。老百姓本来已经被搜刮得叮当响,哪里还能挤出这个钱?加之春耕在即,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以工代款,也万万行不通。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老百姓只剩下硬抗一条路,谁也不去出河工。
布告张贴了两个月,马颊河疏浚工地依然空空如也,看不到几个人。傅奎升整日在县衙里团团乱转,拍桌子,砸板凳,指斥下属无能。县警察局命警察队下乡催逼农民出工,见到在田里劳作的农民就撵着去上河,谁要是说不去,一阵皮鞭就落在身上,“谁敢反抗,就抓他到大牢里开开荤!”警察们咆哮着。就这样,不少农民被驱赶到了疏浚工地,满怀愤懑地干活。一时间,反抗情绪涌动于全县城乡。
胡恒熙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从得到的信息分析,他越来越清晰地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席卷而来。他召集县委骨干成员,研究如何因势利导,领导好这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大家一致同意,决不退缩,彻底揭露官府贪污腐败的恶行,抵制当河工;当下首要任务是组织农民成立罢河工后援会,一家被抓,众人援助。
会后,一区区委书记、胡恒熙的侄子胡林晓跑回龙王庙村发动群众:“要罢河工,只靠一个人反抗不行,必须联合起来!一个人,十个人,反动政府能抓起来,要是我们都反抗,他们还能抓吗?”
有人问:“要是被抓起来,俺的地谁来管啊?”
胡林晓说:“谁被抓起来,我们就帮着他家种地,大伙一块想办法救人。”
有人忧心忡忡:“咱都是草民,自古就是民不跟官斗,咱这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吗?”
胡林晓说:“这种想法要不得!如果我们都这样想,高兴的是官家。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跟混账的官家干,才有活路!”
群众纷纷说:“政府不让咱活,就跟他们拼了!参加后援会,给俺报个名。”
“咚咚锵——咚咚锵——”昂扬的锣鼓声一扫阴霾,龙王庙村的后援会成立起来了。紧接着一区的马刘家村、徐波罗村、孙良才村、杨家村、耿家村都相继成立了后援会,编造了花名册。
罢河工运动正式开始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