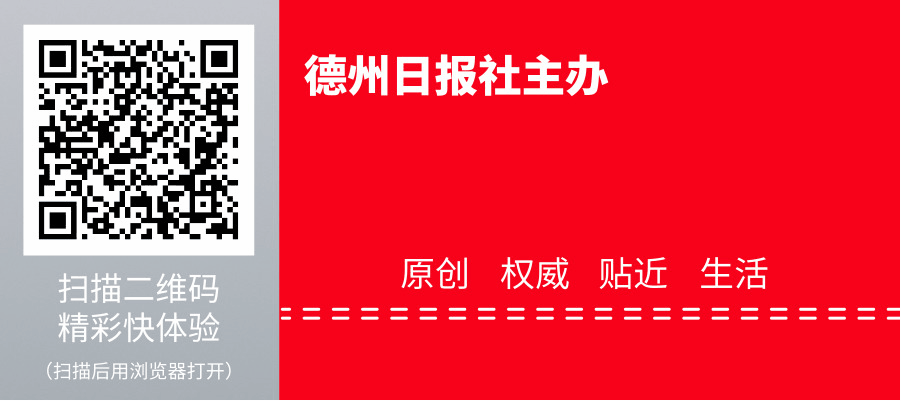活成父亲的样子
文|孙瑞柱
与信仰无关,父亲的身影
隐匿于,远山深处
像一根草
风中低下贫瘠的头
父亲的影子很小
也很虚弱
疏松的骨质
把经年,举过头顶
复制父亲的
相貌,性格,意志
活成父亲
谨慎的样子
庄 稼 汉
文|康丙云
把所有的日子
都种进那几亩薄田
用一生的汗水
为儿女培育温馨港湾
田间地头,一袋旱烟
您的春秋
完全抒写在眉宇间
夏日河流
是一个庄稼人内涵的浏览
一垄垄幼苗
统统安置在柔软的心田
为此
跟太阳的泼辣较劲
给夜半的月光赦免
记忆中,父亲
您从没想过
铿锵的脚步
离开土地一天
父 亲
文|张居明
您是一座高山
令我们终生仰望
总想登上您的肩头
去看无限风光
您是一棵大树
替我们把风雨遮挡
我们在您的荫护下嬉戏玩耍
酷暑里送来一丝清凉
您是一盏明灯
为我们指明方向
前进道路上艰难曲折
再也不会惆怅迷惘
我们就是您亲手栽种的庄稼苗啊
一天天看着我们健康成长
地头上您嘴里衔着旱烟“叭叭”作响
欢乐的花朵开在您的心上
生活才刚有起色
您就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想您的时候
只能在梦中相见
父 亲
文|宗晓猛
父亲啊,父亲
您没有太阳的光辉,却有太阳的温暖
您没有山岳的高耸,却有山岳的伟岸
您没有松柏的长青,却有松柏的劲拔
父亲啊,父亲
您笔直的脊梁撑起了家庭的重担
您宽厚的肩膀扛起了妻儿的期望
您有力的双手托起了幸福的重量
如今啊,父亲
时光在您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岁月将您的头发褪去了乌黑的颜色
生活在您的眼里注入了人生的故事
但是啊,父亲
您在身边,是驱散黑夜的光
您在身边,是醒聩震聋的钟
您在身边,是遮风挡雨的伞
纵使日薄西山,您仍是我的英雄
纵使峻山无棱,您仍是我的榜样
父亲的草原(新韵)
文|王存昌
几曾梦里念呼伦,
阔野依依驻我心。
朝露凝结原上草,
暮风摇曳马头琴。
父亲放远长鞭响,
红日巡高细水吟。
岁月有情歌塞外,
蓝天深处唤云魂。
致父亲节( 新韵)
文|耿金水
海动山倾凭臂膀,
寡言负重鬓秋霜。
曾经教我识荣辱,
几度传书论短长。
回看当年犹感慨,
遥知一笑也飞扬。
半生转瞬沧桑路,
挺起全家作脊梁。
夜色中的背影
文|王凤华
父亲是我们县第三中学的校长,教了一辈子书,平时不苟言笑,看上去不怒自威。小时候同学去我家之前,先问“你爸爸在家吗?”如果我父亲在家,同学们就怯于来我家。
那时候,父亲每天忙于教学和学校的管理。无论多忙,父亲都会抽出时间来关心我们。当我们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父亲会在第一时间疏导我们,找出原因,鼓励我们,在父亲的激励下,我们每次都会从愁眉不展到自信满满。
我考入潍坊电校第二年的国庆节,回家后由于贪吃母亲做的好吃的,也是磨蹭时间愿意和母亲多呆一会儿的缘故,当父亲骑着自行车把带着大包小包东西的我送到县城汽车站时,错过了最后一班夏津开往平原的汽车,因为从平原县坐火车才能到潍坊。那时候没有手机,信息闭塞,连公用电话都不普及,没法向老师请假。
正在我心里慌张不知所措时,为了不耽误我正常上课,父亲决定,骑自行车送我去平原县。
我和父亲先在夏津县城吃了点饭,天还没有黑。父亲骑着二八的“飞鹤”牌自行车带着我,车把上系着包,我背着包,往平原县城的方向骑去。那是一条土路,不时会有坑洼颠簸一下,一路上,骑一会儿,歇一会儿。渐渐地天黑下来了,我们又感到了饥饿,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于是就把母亲给我带的那些吃的东西拿出来吃点,喝几口水,继续骑车往前走。月亮升起来了,洒下一路皎洁的月光,我坐在后面抬头看,仿佛能看见月里的嫦娥,她微笑地注视着我们父女,给我们带路。秋天的夜晚,一阵阵凉意袭来,怕我冷,父亲把他的外套脱下来给我披上,我顿时感到了温暖。父亲出了一身汗,身上散发着热气,月光下我看见父亲头发上升腾着细小的汗雾。
初秋的田野,有秋虫鸣唱,不知是蝈蝈还是蛐蛐。不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蛙叫,成片的玉米有一人多高,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看上去影影绰绰,我不禁害怕地把脸靠在父亲的后背上,父亲的后背是温热的湿漉漉的,我拽着父亲衣襟的手更紧了。父亲感到了我的恐惧,于是下车,我们找一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入夜后的庄稼和草叶上挂着露珠,青草掺和着花的香气钻到鼻子里,是秋的味道。父亲给我讲起他中学时穿过一片坟地去上夜自习的经历,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鬼神,都是自己吓唬自己,渐渐地我的心情放松了。父亲又蹬上自行车带着我向前走,慢慢地变得吃力,上坡的时候,车把有些摇晃,父亲努力地前倾着身子往前蹬。看着父亲吃力的被汗水浸湿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
走走歇歇,骑到平原县火车站的时候,天快亮了,我们走了整整一夜。打发我上车后,父亲又匆匆往回赶,还要去处理学校的事务。后来据父亲说,往回骑了一半多的时候,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就倚着路边的树睡了个把小时,我不禁有些心酸。
从小到大,父亲用执着深沉的爱呵护着我们,用他宽厚的脊背为我遮风挡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有父亲在,我就有底气,父亲就是我可以依靠的山。
多年来,那个初秋的夜晚,父亲一路骑着自行车送我的画面,清晰的印在我的记忆里,月光下,父亲的背影那么伟岸、那么温暖……
沐浴阳光
文|闲云落雪
雨停了。我搀着父亲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活动一下僵硬的四肢。手术后的父亲非常孱弱,原本就不灵便的双腿看起来更加蹒跚。我一手扶着他,一手指给他看路边那棵高大的丁香树,满树的丁香花正在盛放,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芳香。一道阳光突然冲破云层,从树叶的缝隙间流泻下来,参差斑驳,落了我们满身满脸。
父亲眯起眼睛,向着阳光的方向望了望,满头银发在细碎的光线里颤动。他微笑着,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一出来,立刻就觉得热乎乎的了。”
是啊,太阳出来了,浓重的乌云被迅速驱散,天空一派澄碧。阳光照拂下的树木花草显现出无限生机,那一线自假山飞落的小溪似乎都欢腾了起来,哗哗地唱起了歌。我的心也唱起歌来,这些天的苦痛、压抑和郁闷,都随着父亲的那抹微笑而烟消云散了。
半月前,父亲被怀疑得了乳腺肿瘤,仿佛晴空一声炸雷,把我们惊在当地,乌云翻卷着,遮蔽了晴天丽日。更受打击的是父亲,他仿佛被击倒了,所有的精气神一下被抽走,眼神变得暗淡无光,面色沉滞凝重得厉害,背也更驼了。
去济南复查的那天清晨,我们站在路边等舅舅,父亲一个人坐在车里。透过车窗,我看见他蜷着身子,把头抵在前面的座椅背上,满头白发显得格外耀眼,肩膀微微耸动,看上去无限落寞而衰弱。我的眼泪刷地溢出眼眶,恨不得冲上去打开车门,将他深深抱住,给他一个支撑,可我不敢,不敢撞破他刻意躲闪的萎靡和脆弱。
等待结果的日子是最难熬的。父亲和我们的心里都揣着一块巨石,可又不得不故作轻松,各自给对方宽心却虚假的微笑,就像等着宣判的犯人,忐忑不安,忧心如焚。
手术那天,全家人都赶了去。就在手术前一刻,院方通知我们,基本排除癌变可能。我们揪成一团的心终于舒展了些,母亲更是高兴成了泪人儿,对着父亲的肩头不停捶打。手术很顺利,活检结果也出来了,只等乳头乳晕的检测了。就在刚才,我们正要出门散步时,主治医生送来最终结果,彻底排除癌变。
父亲似乎有些不相信,询问地看着医生,医生微笑着又重复了一遍,父亲的腰板不由得直了直,抓起医生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然后不顾我的劝阻,把原本走廊里的散步,执意改到院子里。
“回去吧,我累了,读会儿书去。”父亲轻轻拍拍我的胳膊,把出神的我唤了回来。
读书是父亲住院期间才设定的“必修课”。刚做完手术那两天,父亲很疲倦,经常昏昏沉沉地睡着,后来他的精神逐渐恢复,也不用输液,就变得无所事事起来。他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着,一会儿看看引流瓶里的液体增加了没有,一会儿问几点了,一会儿担心弟弟的小店忙不过来、俩孩子是不是听话,一会儿又说不知你娘去打柔力球了没……一副百无聊赖、度日如年的样子。
在父亲又一次索然无味地躺下休息之后,我随手拿起父亲的手机胡乱摆弄,却发现了一样可以让父亲充实的好东西——电子书。父亲教书育人一辈子,书和笔是他最大的爱好,我何不借这个机会,挑选几本父亲喜欢的小说,读给他听呢!
父亲显然很高兴,他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儿,还不时地发表看法,如果我有事,他就拿过手机接着读。一部中篇小说就在我们“夹叙夹议”的阅读声里“看”完了。
对了,还可以跟他一起“研究”宋词。这次来住院,父亲居然带来了他平时练书法时抄的宋词,是几页叠得整整齐齐又裁得很小的纸片儿。
那天晚上找水果刀,我偶然发现了这个“小秘密”,它们静静地躺在抽屉最里面的一角。好奇地翻了翻,竟然都是草书,我几乎完全不认识。父亲看着窘迫的我笑了笑,伸手拿过纸片:“草书太难认了,我学的时候可费功夫了!来,我教你。”父亲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兴致勃勃地坐起来,斜靠在床头柜上。
父亲一面念,一面讲,因为对有些典故不了解,有几个地方断词断句不准确。我笑着给他纠正,并给他讲解那些典故的含义和诗词表达的意境。父亲听得极其认真,不断“哦哦”着,还细心地用笔做着记录。讲到《江城子·密州出猎》和《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父亲恍然而开心地说:“我原先一直弄不明白‘左牵黄,右擎苍’、‘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和‘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马作的卢飞快’是什么意思,这下终于知道了,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哦。”他又从头仔细看了一遍,一面圈圈点点,一面感慨道:“老啦,记性不好了,我得再复习复习。”
依稀回到了小时候。我和弟弟规规矩矩坐在堂屋小凳上,前方不远处的墙上,挂着一块儿小黑板,父亲在上面写写画画,讲经典的追击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把同向和相向搞混,父亲很生气。母亲把饭菜端上了桌,香味逗弄着我们,肚里好像有上百只爪子在抓挠,我和弟弟坐不住了。父亲声色俱厉地喊母亲把饭菜端走,并最后通牒道,学不会这个问题,不许吃饭。我和弟弟正襟危坐着,眼里含着委屈的泪花,手里的笔却写得更起劲了。
或许父亲始终沉浸于教师的角色,也或者在他眼里,“父亲”和“教师”二者就应该等同,印象中,他总是严肃和不苟言笑的,我们一度很怕他。吃过晚饭,母亲去洗刷了,父亲躺在炕上,把我们喊在他身边,给我们讲成语小故事。也只在这时候,父亲是亲切而随和的。像什么叶公好龙、画蛇添足、杯弓蛇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亡羊补牢……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都是在那时候,刻进了我们的记忆。
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又恍如隔开了一个世纪,只是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的眼神里少了严肃,平添了许多温柔和宠溺,还有依赖。我们的角色,似乎互换了。
回到病房,临床不在,屋子里静悄悄的。我和父亲相视一笑,再次踏上我们的文字之旅。今天应该是第二部了吧?管他呢,父亲快乐就好。读着读着,父亲发出轻微的鼾声,他睡着了。我轻轻合上手机,轻轻给父亲拉了拉被角。
父亲睡得很沉很安稳,这可能是他这些日子来第一个好觉,面色透着些红润,纵横交错的皱纹,似乎也浅缓了些。细想起来,像这样近距离地端详父亲,静静地看他安详的睡姿,这还是第一次。是从什么时候,那个不知疲惫、从不服输、从不懈怠的父亲,开始变得步伐迟滞、目光飘忽?变得如此苍老、衰弱?
我小的时候,爱流鼻血,为此没少求医。最严重的一次,无论如何止不住,把鼻子堵上,又从嘴里流出来,终于昏迷不醒。父亲连夜骑车到几十里外请来大夫,打上强心针,才救了过来,稍微好些,又带我去省城的大医院。路没少跑,什么都没查出来。在省城求医的间隙,父亲带我去拍了一张合影,是一张两寸的黑白照片,小小的相纸上,只有两个圆圆的脑袋,唯一不同的,是父亲明显瘦削而我略显丰腴。
初中开始,我去了离家五十多里的县城求学。原本平整的土公路,经过长时间车来人往的碾轧,上面有大约半尺厚的浮土,自行车骑上去,就像轧到松软的海绵上,每一步都特别费力。父亲一个月来接我一次,周五下午接,周日下午送,风雨无阻。来接我时,顺带把我的口粮捎来——几十上百斤麦子,交到司务处,换出饭票。都说远途无轻载,何况父亲三天要两个往返。多年以后,我自己骑车上下班,才体会到当初父亲的艰辛,而那时,已经是柏油路了。
记得每次回到家,父亲后背的衣服都会湿一大片,屁股上也是湿的,进门胡乱擦把脸,就趴到床上,半天不起来,吃饭时总半侧着身子,仿佛悬空着,坐不安稳。我问父亲怎么了,他避而不答。后来跟母亲说起,才知道父亲屁股上起了血泡,有时甚至都磨破了,他是根本没办法坐下。
大弟也很早就去外地上学,他上学的地方更远,离家有八十里,后来又轮到了小弟。我们辗转到哪里,哪里的公路上就会出现父亲奋力前行的身影。
再后来,我们姐弟三个相继成家立业,相继有了自己的孩子,父母又开始为第三代劳心劳力。风风雨雨几十年,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缕阳光的照拂,习惯了他的温暖和呵护,习惯了他的强大和威严,竟是完全忽略了,这缕光也有疲惫的时候,也有老去的时候,他也需要我们的照拂。
“3床,换瓶子了。”年轻的护士推门进来,笑盈盈地走到父亲床边,从布袋里掏出引流瓶看了看,“已经不多了呀,恢复得不错。看样子,大爷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我真的很快就能出院了?不会再反复吧?真好,真好!”父亲一下来了精神,确认似的低声重复着,迫不及待地摸过手机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
有滚烫的液体缓缓流过我的脸颊。这的确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声“快要出院了”,宣告着噩梦般日子的结束,宣告着我们爱的天空里,重新阳光普照!一缕夕阳不失时机地挤进窗帘,依着窄窄的缝隙,不动声色地流泻进我的怀抱,温柔、和暖、轻巧,我闭起双目,深深地醉在它轻柔的抚爱里。
德州日报全媒体出品
来源 | 德州市作协 编辑 | 李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