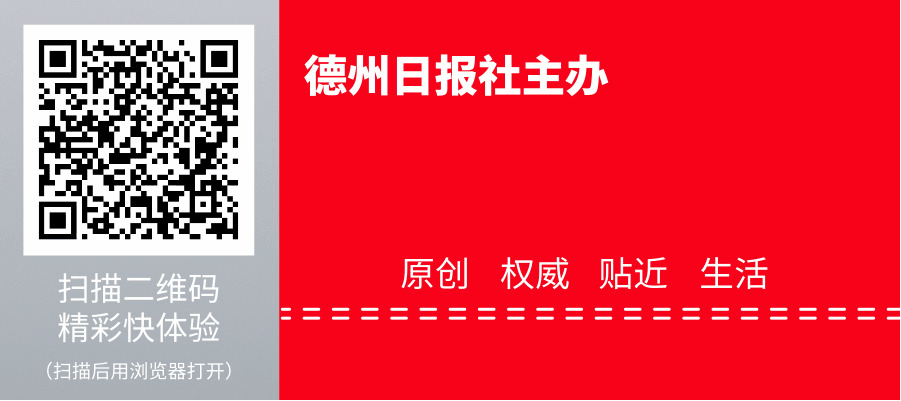文 | 王兴海
我早就想写一写我的父亲。曾经练习写过一篇《父亲上学》,我不怎么满意,因为只是写了父亲年轻时候的一件事。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我被父亲的生命力感动,所以想到了写一写父亲的生命力。
一
父亲生于1936年,这由父亲的属相可以知道,至于生于哪个月,我奶奶和爷爷已经记不清了,他们只是说生在拔棉花柴的时候。后来父亲自己推测,那时候的棉花柴不像现在摘完了棉花就拔,过去都是在地里待到冷时候的。父亲后来填表什么的就确定为农历十月,阳历就为11月。具体哪一天呢?奶奶说村里有一个与父亲出生相差4天的人,不知谁早4天。后来父亲去问那人的父母,到底两个人谁早4天,谁晚4天。那人的父母回答,“不是你早4天就是他早4天。”这等于没说。但在这里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那人的出生日期是在农历的十五日。那么从这里判断,父亲的生日应该是农历某月十一日或十九日。父亲后来查了一下《万年历》,自己确定了身份证上显示的出生年月日19361119。父亲从没有算过卦,他没法告诉按生辰八字算卦的盲人的准确信息。如果父亲说了自己选定的生日时辰,也许这个的命运跟村里的傻二是一样的呢。
父亲出生的时候命运不好,他一出生就有脐带缠绕在脖子上,没有来到世界上的哭声。接生婆提着两个小腿又拍又捏又抠嘴,小身子都发紫了,好歹发出了哭声。
爷爷的家庭是贫穷的,穷到没有粮食。奶奶没有奶水,爷爷就只有看着父亲整日的大哭。
爷爷搓着手,屋内屋外的走动,一次次地说:“有啥办法呢?”
父亲瘦得看到骨头,小肚子里的肠子都显露出来。奶奶也看不到一丝希望了,无奈地说:“看来养不活他啦。”
后来爷爷终于弄来一捧蜀黍,他在板子上用擀面杖轧成面,然后熬成糊糊抹进父亲的嘴里。父亲活了下来。我小的时候不知奶奶给我说过多少次:“你爹小时候是用一捧蜀黍糊糊抹活的。”
二
我不妨把我的《父亲上学》放在这里,你先耐心地了解一下我父亲的一段情况,然后我说一下父亲一生里的一个重要节点。
父亲上学——
父亲正走在路上。
他脚下的路像耄耋老人脸上的皱褶,向父亲显示着车轮碾压过它的痛苦。父亲的脚板下像有针扎似的,一不小心踩在路的皱褶上,又像触电一样几乎被击倒。
与父亲一起走在路上的,是村里一位像他一样的青年。这位青年对父亲说:“我们不去报了,往回走吧?”
父亲说,“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吧。”他继续走。
父亲手里有5块钱,是1954年时候的5块钱。5块钱是父亲在聊城专署当通信员的哥哥想法筹到的。那天,爷爷一家聚在正房里,如豆的油灯光照在一家人昏黄的脸上。
爷爷说:“不要去报了吧?”
奶奶说:“我们去哪里弄钱呢?”
大伯说:“去报吧,钱我去想法子。”
有了大伯的法子,父亲才走上了这条去聊城的路,一条140华里的“皱褶”。
父亲终于走下来这条路,找到了他要报考的初中学校。可学校的门是关着的,一片的寂静。等见到一位年老的看门人时,看门人告诉父亲:“报名已经结束啦。”
父亲像气球撒了气一样瘫软在地上。
与父亲一起走在路上的村里青年说:“我们再回禹城报。”
父亲和青年又走在去禹城的路上,这条几乎也是140华里,也是像耄耋老人脸那样的路。
这回是父亲失去信心了,他对村里青年说:“我们不报了,回家吧。”
村里青年却说:“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再坚持一下。”
父亲走到一座小桥上,见石头有些平,就急不可待地平躺在石头上。他闭上眼睛,感觉到脚和腿的疼痛布向全身。
村里青年催促父亲:“我们走吧!”
父亲睁开眼,坐起来,将左脚上的鞋一点一点——不是脱下来,而是从皮肉上揭下来。
村里青年再一次催促:“我们走吧!”
父亲穿上鞋,忍着苦痛继续赶路。
禹城这所学校在远离县城的东北角上,像小庙一样的荒凉。当父亲他们走到校门口的时候,遇到像在聊城一样的情景,也是看门人告诉他们:“报名已经结束了。”
这一年,父亲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1955年的一天,父亲独自走在向齐河学校的路上。他是早晨听到第一遍鸡叫起床的,他走出大约20华里后,天才像沉睡的人刚睁开点眼睛。
父亲去齐河报名,去时是顺利的。没想到回来的时候遇到了大雨。雨来得快,下得猛,让父亲没有防备。他走到两个村子之间的时候,雨从天上浇下来,浇得父亲像一只落汤鸡。走到下一个村子,天也暗了,父亲不敢再走,就住在了一个人家。
考试时,父亲又走了一遍去齐河的路。
父亲考中了。前20名的学生张出榜,父亲的名字在第8位。但父亲没有去上。没有去上的原因是头一天家里走进了一个高级社里的人。这个人对爷爷和父亲说,“社里缺一个会计,到高级社里当会计,你们想想是不是比上学好?”一家人沉默了。在社里人即将出门的时候,爷爷替父亲答应下做社里会计了。
父亲在高小学习一直是前两名的,他对念书有一种情结。1956年,他又报考了茌平一中。促使他这次去念书的再一个原因是省里来人查账。
父亲当高级社会计不久,就跟着河工到工地负责账目。没想到有人反映干部有问题,直反映到山东省委。山东省委的人直接找到父亲,要看父亲的账目。父亲从房梁上拿下账本交给省委的人,省委的人查了一天,什么也没说就返回了。
隔了10天,省委的人又突然回来,让父亲再拿出账本,又查了半天后,一个人拿着账本问父亲:“这能与民工见面吗?”
父亲说:“能。”
省委的人便召集起民工代表,一项一项跟民工对证。
省委的人说:“4月份吃了三次细粮,对吗?”
民工代表说:“对。”
省委的人说:“你们写个证明。”
省委的人说:“这个月份共吃了9次白菜,有两次加肉,对吗?”
民工代表合计了一阵说:“对。”
民工代表又做了证明。
时隔几天,省委的人又回来一次,直接找到父亲问:“社长是不是拉了一车木柴回家?”
父亲说:“是拉了一车木柴,但不是伙里的,是村里房东给他的。”
父亲万没有想到省委的人会第四次来。省委的人第四次来的目的是调查社里的干部工作作风问题,有没有打骂民工的现象。
民工代表又一次被集合起来,在省委的人的面前,他们没有说出值得省委的人特别关注的事情。
事后父亲想,还是去念书吧。
父亲考中了茌平一中。
此时父亲已经娶了我母亲,父亲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日,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聚在奶奶的屋里。
奶奶说:“拿什么供你念书呢?”
其他人都没有言语,屋里静静的,只看见父亲的脚在炕前踢过来踢过去。静了好久,奶奶又重复了刚才的话:“拿什么供你念书呢?”
这时爷爷说了一句话做了最后的决断:“不去念啦,过日子要紧。”
父亲两天没有吃饭。
报到的时限过了,学校没有得到父亲报到的信息,很快,父亲收到了学校的一封信,信是用毛笔写的,很漂亮的小楷。——
王方荣同学:
你已达到了我校录取的分数,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你来报到。我们估计你一定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很理解你。当前我们谁没有困难呢?
你在众多的考生中能考中我们学校并取得优异的成绩,说明你是很聪明的,也说明你一定是一个很勤奋、很努力的人。你不能来我校读书,不仅是你的遗憾,也是我校的遗憾。
国家正在建设中,国家建设离不开人才,尤其是需要能掌握更多知识的优秀人才。无数有大志报效祖国的青年人,都在为祖国建设努力求知,想在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从国家的需要讲的。作为自己,一个小学生在家乡算是平常的,而作为一个初中生,就是家乡的佼佼者,一个初中生的前途会更宽阔、更高远。
困难是人人都会有的,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能够想办法克服困难,不要轻易放弃这次机会。你入学后,学校根据你的情况也会对你给予帮助和照顾的。
我们希望在我校看到你学习的身影。
……
信有3页纸,父亲读完,来回在屋里走动,手里的信纸随着他的走动而飘来荡去。他在西屋里透过窗子一次次张望爷爷奶奶居住的正房门,想再一次找到爷爷和奶奶将自己念书的欲望讲出来,可他一次次没有勇气迈出西屋门。他不再在屋里走来走去,而是躺倒在炕上闭上眼静静地一动不动。许久,他猛然起身,冲出西屋门,急步走进了爷爷奶奶的屋门。父亲给爷爷奶奶读了学校的来信。
听父亲读完学校的来信,爷爷只是一口一口吸他的旱烟,奶奶只搓她生有老茧和裂缝的双手。奶奶只会重复她的那句话:“拿什么供你念书呢?”
爷爷磕掉了第二锅子旱烟后对奶奶说:“孩子这么喜欢念书,学校又来信,那就去念吧。一家人来想法子。”
奶奶在炕上把头回到里面偷偷抹起了眼泪。
自从决定了父亲去念书的事,奶奶就准备父亲的学费。她把一点毛票数了一遍又一遍,难以想出其他钱的来路。
奶奶和爷爷、母亲在一个夜晚,坐下来,郑重地商议怎么凑齐父亲念书的钱。
爷爷说:“家里的两只鸡不要养了,拿集上换点儿钱。”
奶奶说:“他姐夫那边陪送过来的一件夹袄能换一点钱儿。”紧接着奶奶对母亲说,“织布机上那块白布咱娘俩倒换着这两天织下来,先换点钱再说。”
终于凑够了父亲念书的钱,父亲实现了他念书的愿望,成为茌平一中的一名学生。
后来父亲对我说,“我到茌平一中后,教导主任亲自找到我把我领到教导处给我谈了一次话,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一开学就宣布我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久,学校又宣布我为校团委副书记。当时的团委书记是我上一级的学生。从学校的安排和学校给我写信这些事上判断,我的考试成绩可能是全级第一。”
父亲在学校生活非常节俭,除了要往学校非缴不可的钱,自己不会乱花一分钱。在可忍的情况下,他都是空一点肚子,少吃一点,省出一点钱。学校附近有一所医院,父亲经常看到在井边有洗药瓶子的人。父亲找了人,在课余时间洗了一阵药瓶子,医院的一位工人一次给他两毛钱。父亲还星期天在附近的工地上推过土,挣到过一块八毛钱。
父亲的第一学期读下来了,第二学期的学费又成为一家人头疼的事。第二学期开学,奶奶没有凑够父亲的学费。父亲去学校的时候,奶奶对父亲说:“给学校好好说说,再缓一个星期,让俺想想办法。”
父亲很无奈地去上第二学期了,奶奶想在一星期内凑上父亲的学费。可是,父亲不到星期天就回来了,说学校催要学费,并且父亲说第二天就返回学校。
奶奶十分无奈地说:“到哪儿去弄钱啊!”
想遍了所有的法子,奶奶凑了一点钱,最后差两块钱怎么也凑不上了。两块钱,难得奶奶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奶奶这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转下来,自言自语地说,这两块钱只有去借了,接着再问自己,到谁家去借呢?把庄里人家数算一遍,觉得只有两家或许还能借出两块钱。一是庄南的吴家。吴家两口子没儿没女,花钱的项少,并且多少还有点来钱项。二是庄西王家。王家的女婿家里日子好些,王家的女儿能对娘家有点帮衬。奶奶再三权衡之后,决定去吴家借这两块钱。离吴家距离稍近一点不说,吴家媳妇的脾气也比王家媳妇的脾气随和些,再说,前两天刚跟吴家媳妇在一块说过两句话。
吴家在胡同的南头,靠门长着一棵高大的榆树,以榆树为界,向东就是吴家的宅子,吴家的宅子高出一大截,从吴家出来要下一个不小的斜坡。
奶奶要去借钱了。兴起了心,外面的雨也没有挡住小脚的她。她拄一根棍子悄悄出去,一擦一滑地走到吴家大门口。她扶着榆树艰难地登上吴家的高宅,怯怯地敲响了吴家的大门。吴家媳妇开了门,奶奶按着庄里的辈分先叫了一声二奶奶,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借两块钱的事。见吴家媳妇的脸色尚好,奶奶的一颗紧揪的心才稍稍放下。
奶奶借到了两块钱,她一再感谢吴家媳妇。吴家媳妇要把奶奶送出大门,奶奶不让,强把吴家媳妇推回去,“二奶奶你快止住步,不要送,不要送!”奶奶出了大门就把大门关上了,阻止了吴家媳妇。
奶奶没有直接走下吴家门前滑滑的坡,而是走到大榆树跟前,想扶住大榆树从一处看起来不滑的地方慢慢下来。不料,奶奶扶着榆树的手滑脱了,奶奶从坡上滑下来,头磕在榆树上,磕出了血。这一磕,奶奶在炕上瘫了8年,直到没了最后一口气息。
在这里我隐去了父亲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父亲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一辆马车。马把父亲撞倒,马车的一个轮子从父亲的身上轧了过去。父亲自己以为会被马车轧死的,父亲却什么事也没有,从地上爬起来扑打扑打身上的土上学去了。
三
那缺粮食吃的年月,地瓜救了不少人的命啊。那时,哪个村里不种有一片一片的地瓜呀。等到收地瓜的时候,地里摆着一堆堆地瓜,人们用筐子、车子运到家里。有的放进挖好的地窖,有的切成一堆堆地瓜片。那时候已经有了切地瓜的机子,人们将整块的地瓜放进上边的漏斗里,用手一摇把手,地瓜片便像大白蛾一般飞出来。为了晒成地瓜干,把院子里、房顶上,甚至庄外的地里都布满了地瓜片,像冬天里下了一场雪。
地瓜干可以放锅里煮着吃,可以轧碎磨成面做成像橡胶一样的窝头。
人们传说,1959年,兄弟三个到肥城寻吃的,寻了两天都没寻到,很沮丧地走在大街上。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时,一个背着半袋子地瓜干的人出现了,三个人就意见很一致地想到抢过那人的地瓜干。三人走近背地瓜干的人,一下抓住地瓜干袋子。那人怎么会轻易让人抢了自己的地瓜干呢,就死死抓住了地瓜干袋子不放手。三人就将背地瓜干的人砸死拖到附近的水沟里。兄弟三人为了半袋地瓜干子要了一个人的命。后来,兄弟仨都判了死刑。
这等于为一点地瓜干子死了四个人。
1960年,鲁西北平原一带的人们好多都到泰安山区贩地瓜干吃。因为平原地带淹得厉害,什么粮食也不收,而山区不至于被大水淹了,还能够产些地瓜。在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不是粮食的地瓜干就成为粮食。后来,甭说是地瓜干,就是菜也吃不上了。有的村子死了人都抬不出去了,因为活着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抬起那沉重的棺材。
村子里有一个叫老五的人。老五与他的一个堂弟从小一起玩耍,一起到地里拔菜,一起做事。
那天,老五找到堂弟:“人们都到泰安贩地瓜干了,你想去吗?”
堂弟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
两人准备了一点路上吃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
两人到泰安没有白跑,每个人弄了一口袋地瓜干,然后就往家赶。
两人走了多半天,由山区走到平原。在平原上到处是不长庄稼的淹地,地里的水井不缺水。
老五太眼红堂弟的那袋地瓜干了,高高的,鼓鼓的,把口袋撑得这里出来一个角,那里出来一个角。老五的眼珠开始转得有些吓人。
老五对堂弟说:“你渴了吧?”
堂弟说:“渴了。”
老五说:“这里有井了,在这里喝点水。”
堂弟看看井的周围没有可舀水的东西,问老五:“怎么喝呢?”
老五说:“你拉住我的脚,我头朝下来喝,然后我再拉住你的脚,你再喝。”
堂弟按照老五说的做了。堂弟将老五的两只脚紧紧拉住,老五将头伸到井里。堂弟问:“哥,你喝着了吗?”
老五答:“喝着啦。”
之后,老五又拉住堂弟的脚。当堂弟快要喝着水的时候,老五的眼光又落到了堂弟的那袋地瓜干子上。老五的眼里生出一些凶狠。
堂弟对老五说:“再往下一点儿!”
老五把堂弟往下落了一点儿。
当堂弟喝够了水说:“哥,我喝好了,拉我上去吧!”
老五什么也没说。
堂弟又说:“哥,我喝好了,拉我上去吧!”
老五却松开了拉着堂弟双脚的手。
老五背着两半袋子地瓜干回家了,他谎称跟堂弟走散了。没想到,夜里堂弟竟回到家来。
你会猜到这个“堂弟”是谁吗?他就是我的父亲。
四
2017年6月26日,父亲吃过中午饭,睡过中午觉,对我母亲说,“你不是想理发吗,现在去。”他说着就从大门洞子里往外倒三轮车。他把三轮车调整好,让我母亲坐上去。他要骑上去的时候,突然说,“我怎么难受起来了呢?”随着,他就说上不去三轮车了。没什么大事,父亲是从不麻烦我的,说我工作忙不好抽身。这次,他催着母亲给我打电话,并且让我快点来。
我很快赶到了。我问父亲哪里不舒服,父亲说不上哪里难受。我打了120急救电话。
进了县医院急诊室,医生一再问父亲哪里不舒服,父亲说是肚子。
“中午吃的什么?”医生问。
“吃了几块鸭肉。”
“鸭肉新鲜吗?”
“前天买的。”
“是不是坏啦?”
“吃着没什么事啊。”
医生说:“不敢保证你吃的鸭肉没有问题,说不定是食物中毒。老年人都是这样,过过穷日子,什么也舍不得扔掉。”
医生安排了住院,按着食物中毒进行检查治疗。
治疗了几天,父亲还是难受,并且几天也没解大便。再一查,竟是肠梗阻。于是医生采取灌肠的办法,大袋小袋的白色液体从身体后面灌进去流出,灌进去流出。灌了一次又一次,竟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又拍了几张片子后,医生说:“得做手术。”
我就说:“只要能治好病,什么办法都行。”
后来又查心脏,医生说:“老爷子的心脏问题很大,年纪又这么大了,做手术很危险,只能保守治疗了。”
我说:“能保守治疗,最好不做手术。”
又过了几天,父亲排气排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实在沉不住气了。这么多天肠子不通气、不能排便哪能行啊。医生见我总是着急,便说:“转到省医院吧,大医院总比我们办法多。”
我就立即办手续收拾东西转院去省城。
在救护车上,父亲处于半昏迷状态。我问他话,他不回答,我问多了,他有时睁一下眼。
两个多小时以后省城医院到了,我和医生把父亲抬到检查室的时候,发现父亲排出两块蚕豆大小的大便。我惊喜地对医生说:“通了!通了!”
父亲在省医院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周回家了。虽然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生活没问题。
父亲的一位同学懂医学,见到父亲说:“肠梗阻,阻住5个小时肠子就变黑,你阻了七八天竟没要了你的命,奇迹!”
2017年7月30日,也就是离父亲的病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父亲又觉得胸胀,又住进了县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发现肺部有积液,并且是血性的。医生对我说:“血性积液很不好,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一再向医生询问,想弄明白病的情况,医生不得不说:“癌症才有可能出现血性积液。”
经过几天的治疗,父亲的病没有好转。令医生头疼的是肺部积液不是在一处的。医生给我解释说,像一张网一样,这里积一点儿,那里积一点儿,县医院的水平无法解决。
父亲又转到省医院。在那里又进行了一番拍片检查后,医生就在病房里用长长的针从父亲的后背插进去,吸出了肺部的积液。我想象,那条长长的针一定是把父亲的肺搅得乱七八糟,不然怎么能把一个一个网眼里的积液抽出呢?吸出积液,父亲的精神明显见好,也住院不到一周就出院了。很快就跟正常人一样赶集上店。
2017年8月5日,也就是离上次出院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父亲突然大喘起来,第3次进了县医院。这次县医院一查,没有留下住院,就直接让转到省医院。到了省医院一查,就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
父亲在重症监护室里,我一天里只有下午3点之后见半个小时。父亲的双手被绑在床上,口鼻上带着呼吸罩,话也没法说。
“爸!爸!”
我叫他,他没法回答。有时看我一眼,随着就睡去了,像昏迷一样。
再后来几天在重症监护室里见父亲,他大口大口地喘气,感觉很痛苦的样子。
我失望了。医生也说:“你要做最坏的打算。”
我对医生说:“现在我父亲感觉不到痛苦吧?”
医生说:“是的。”
我说:“既然病没有办法治疗了,请不要让我父亲痛苦,好吗?”
医生说:“我们理解。”
十几天过去了,父亲的病仍没有好转,医生失去信心了。医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很客气的让我坐下要谈谈父亲的情况。我坐下后,他望着我好久没有说话。后来他说:“应该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应该用的药我们也用了,老人已经到了这个年龄,这种情况不如带点药回家维持一段更好。这是我的意见。”
我一想,遵从医生的意见吧。父亲就是死也死在自家的屋里,死在自家的床上。父亲就出院了。进了家门,我把父亲安排在床上,就找村里人打听去哪里买寿衣、买棺材什么的,打听村里的丧事怎么办法。我要做好一切准备。
父亲回家后的第3天还是昏迷的,可到了第4天居然睁了一下眼。我凑到父亲脸上叫:“爸!爸!”
父亲的手也动了。
“爸!爸!”
父亲竟示意要喝水了。
又过了一天,父亲很清醒了,可以喝点稀饭了。之后,一天天渐渐好起来,由躺而坐,由坐而下床行走,一个月后竟拿起铁锨掘他的小菜园了。
有人跟父亲开玩笑说:“阎王爷好讨厌你啊!”
父亲也幽默地说:“80年前他就不要我!”

王兴海,男,山东省禹城市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山东省禹城市作家协会主席。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当代小说》《滇池》《百花园》等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200多篇。有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选用或获全国、省级奖。
德州日报全媒体出品
来源 | 史志花开 编辑 | 李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