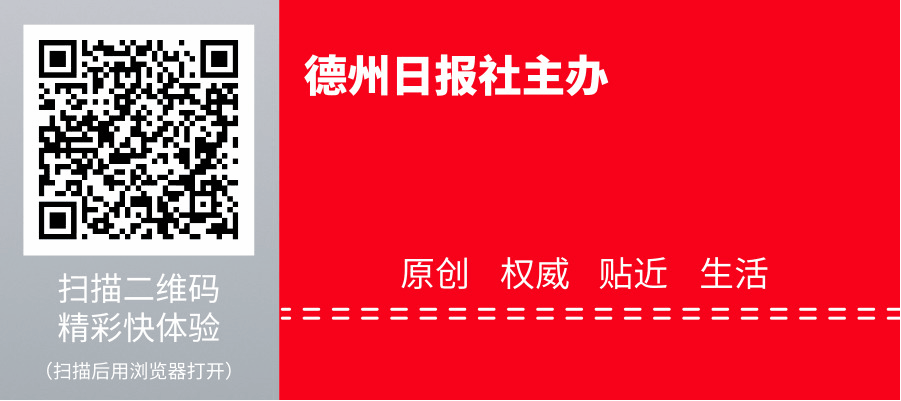老去的村庄
文|莲韵
顺着一朵牵牛花,或者一条长长的瓜蔓爬行的方向,很容易触摸到我儿时的故乡。
几间土坯房,一扇旧柴门。
丝瓜将长长的藤蔓爬到墙头上,举着金黄色的小喇叭,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里,向暖而吹。几只麻雀在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梧桐树上,飞来飞去地欢叫着,姥姥踮着小脚踩着细碎的步子,用一根树枝追赶那些偷吃粮食的鸡们鸟们。……这就是我童年的时光。
低矮的坯房,缕缕袅袅的炊烟,一湾清凌凌的池塘,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天边,几声倦鸟归巢的叫声,划过宁静的天空。村南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上,闲散地走着荷锄而归的老农,还有他身后慢悠悠的一头牛。
这就是我家乡的原风景,它像一幅温馨恬淡的水墨画,无论时光如何辗转,它永远是我梦里挥不去的眷恋。
我的家乡坐落在鲁西北平原。这里没有巍峨的群山,也没有绵延的峻岭,有的只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一年四季,风景各异。春来桃红柳绿,夏来绿茵如海,秋来五谷丰登,冬来白雪皑皑。我爱着家乡的一切,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水一土,都承载着我童年那么多美好的记忆,雕刻着无数的幸福与甜蜜。
到处疯玩。乡村的天空,是那么高,那么蓝,还有那一年四季的风,不倦的吹着。在绿绿的田野上,从南吹到北,从春吹到冬,浩浩荡荡,阳光在广袤的旷野上洒下一片金黄。
桃红柳绿的时节,麦苗返青了,小草冒出了嫩嫩的绿芽,一年之计在于春,大人们开始忙碌着浇水施肥。我们折一枝鹅黄嫩绿的柳枝,修剪成笛,在一片绿色的海洋里悠悠吹起。一边玩,一边采摘田野里那些鲜嫩的野菜。那边是大人们浇地机器的马达轰鸣,这边飘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直到暮色四起,还意犹未尽,干脆脱掉了鞋子,玩起了游戏。
这种游戏我们称之为打鞋拍。就是将所有的鞋子都站立着排放在一起,然后留下一只鞋来,每个人轮流用这一只鞋,站在某个指定的距离之外,开始投掷。如果谁投中了,打散了那些围拢在一起的鞋子,谁就赢了。光着小脚丫,在绿色的麦田里,踏着松软的泥土跑来跑去,乐此不疲。
这个游戏玩腻了,再换一个。因为黄昏降临的时候,天空越来越暗,蝙蝠就会出现了,这种鸟儿喜欢钻洞,把鞋子高高地抛向空中,它会追赶着鞋子飞下来,不过它非常聪明,待到鞋子快要落地的时候,它便很快飞走了。所以害的我们一次次把鞋子抛向天空,累出一身汗来,却最终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一直到夜色笼罩了茫茫的原野,村里上空飘起了缕缕炊烟,炊烟里远远地传来了母亲的呼唤,这时候,我们才捡起那满是泥土的鞋子,恋恋不舍地离开,回家又免不了招来母亲的责怪。
说起野菜,春天里最好吃的就是苜蓿了。尤其是第一茬,又鲜又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是最好的美味了。母亲将它摘干洗净,然后切的细碎调成馅,烙成合子或是蒸成包子,尽管没肉,但却鲜美无比。
那时候只有少数人家种苜蓿,多是在河沿上,成片的也有,不多。那些鲜嫩的苜蓿,就像鲜美的瓜果梨桃一样,诱惑着我们小小的心,顾不得母亲的叮咛,趁人家不注意就去偷。因为知道,即使被人家遇到了,也不会责怪的。
许多好玩的游戏,都是我们亲力亲为。丢沙包,踢毽子,跳方格,打尕,弹溜溜,滚铁环,打弹弓等等。这些都是自己动手,就地取材,不用花一分钱,却给了一个童年满满的幸福与快乐。夏日炎炎的午后,在村南的小河里逮鱼、捉泥鳅,冬日长长的夜晚,就着一轮橘黄的明月光,在大街上,在高高的麦秸垛上,看星星,捉迷藏。
一到晚上,姥姥便在暗黄的煤油灯下,轻轻地转动着纺车,随着吱吱呀呀的声音,一根长长的线永远也纺不完似的,仿佛在转动着那悠长的岁月一般,永无尽头。母亲则在炕上给我们做棉衣、或棉鞋,看到那些白白软软的棉絮,心里便暖暖的。想着过年又可以穿上新棉袄、新棉鞋了。还有那些长长的棉线,还可以织成布,再印上花,母亲还可以做一件花衣裳给我了,真好!
小时候总是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带花帽,吃水饺,放鞭炮。特别到了年市上,买一条向往已久的红绸子,系在发梢上,心里那个美哟!记得我曾经亲手缝制了一个小小的布袋,把我心爱的宝贝都装在里面,几条红红绿绿的头绳和绸缎,一个沙包,几只大大小小玻璃球,几枚古董味的铜钱等。这些都是我的心爱之物,我会时不时拿出来去炫耀一番。
院中有一个四奶奶,我经常跟母亲去她家玩。四奶奶是小脚老太太,人长得端庄优雅,衣着朴素却非常得体干净,屋子里总是打扫的一尘不染。一张旧式的八仙桌,两把圈椅,桌子上始终摆放着一把老式圆柱形的茶壶,放在一个特制的保暖圆型套子里,然后再用毛巾盖在上面,喝一碗倒一碗。所以我一直感觉四奶奶是个活得滋润而精致的女人。一辈子精明能干,却嫁给了老实巴交、不善言谈的四爷爷。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没有一男半女,后来过继了一个女儿。
四奶奶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每当秋末总会挂满一树红红的枣子,特别诱人。那些又脆又甜的红枣便成了我的美味,吃着吃着,临走还要给我带上一些。我每次去她家,总是惦记着那些好吃的,四奶奶会从她锁着的柜子里,拿出几颗糖块来,以及花生等等。
冬天,她还会端出一碗自己制作的醉枣,我一边吃着,一边听她们唠家常。我至今保存着一张老照片,是父亲照的,四奶奶一家和我们一家,每次看到它,就好像又回到了那遥远的童年,感慨万千。
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电灯,没有玩具的年代,物质极度匮乏,精神上却是那么饱满富足。许多的快乐和幸福,是如今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那时候的书包没有现在这么沉重,那时候的天空没永远是碧蓝碧蓝的。那时候小河里的水是清澈干净的,没有半点污染,那时候人心是单纯的,快乐是简单的。
从前,光阴总是那么慢,那么闲……
记忆最深的是村南头的那口老井,和那一湾清澈的池塘。池塘的四周种满了树,柳树、榆树、杨树、枣树,还有几棵老枣树。池塘的东南边上种植着一片茂密的芦苇,水鸟,蓝天,白云,微风一吹,沙沙作响,浩浩荡荡。这一片池塘和树林,成了我们那时的乐园。
童年的夏天,总是那么长,永远也过不完似的。我们在池塘里快活地玩耍,捉小鱼、小虾,还捉泥鳅。水多的时候鱼虾不容易捉到,要等到天旱得不行了,水很浅了,远远地能看到鱼在那里游动。我们便挽起裤脚下去,有幸可以逮住几尾小鱼。泥鳅隐藏在淤泥里,水干了的时候,只剩下一片湿地,便可以循着泥鳅钻洞留下的痕迹,挖下去,就能逮到它。这东西太滑了,稍不留神,它就会从手里溜出去。
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在这片幽静的树林里寻找蝉狗。夜晚的乡村,格外的宁静,格外的迷人。月亮掉在水里,波光粼粼。蛙声此起彼伏,夏虫在歌唱,到处是大自然美妙而动听的乐章。蝉狗这时候已经爬上了树,沿着树干或树枝梢上,可以找到。幸运的话,一晚上捉到几十个,兴高采烈地捧回家。
母亲把它们洗净后,撒上盐,腌制一晚上,明天再用油煎熟了,可年少的心总是疏于等待的,赶紧用脏兮兮的小手捏起来,顾不得烫,放进嘴里,又脆又香,真是美死啦!
记忆中,每家的院子里,总会种着几棵树,杏树,梨树,而枣树最多,几乎家家都有的。村里有几处成片的枣树和梨树,我们称之为枣树行子,那是旧时大户人家祖上遗留下来的。而我家没有枣树,所以村边的枣树行子便成了我们最快乐的向往。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经常溜进那里,那些青涩的果子藏在浓密的叶间,隐约可见。于是一个个猴一样爬上去摘下来,咬一口,涩涩的,不好吃,便扔掉了。害的小脚老太太,老远地用拐杖敲着地,尖声地骂我们。不等她赶来,我们早就像鸟儿一样飞走了。
池塘那片树林里,还有几棵枣树和梨树。那是别人家的,那家有个老太太,长得又矮又胖又黑,平时总是一副冷面孔,从来没见她笑过。因为她家成分高(地主),我们就暗地里给她取了个外号,地主婆。其实,没少去偷她家的枣和梨。几个孩子爬到树上,专挑那些熟的通红的枣往兜里塞,我不会爬树,就拿了根竹竿打,那红红绿绿的熟的不熟的,落了一地。
直到听见小脚老太太老远的叫骂声,我们便一哄而散了。有时候也去摘梨,那还是青涩的果子呢,不熟,咬一口便扔了,因此没少挨那老太太的骂。每逢在路上碰到,她总是黑着脸瞪着眼骂我们:熊孩子!虽然惹她生气,但枣子成熟的时候,她总会给我家送一篮子来。因此,在那个缺衣少吃的年代,那又脆又甜的红枣,便成了我最大的诱惑和美味。我的童年,就这样甜甜地走过来了。
在池塘的东上沿,是那口老井。地势比周围高,井沿和地面一平。这是村里唯一的一口甜水井,几乎家家户户、远远近近都是吃这口井里的水,做饭,洗衣。饮牲口,也是靠这口井。老井是什么年代修建的,说不清了,听爷爷辈的说,从他们那时候就有。老井直径有一米多,四米多深。井壁是用那种年代久远的青砖砌起来的,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打磨,井壁上早已覆盖上了一层墨绿色的青苔。地面是用砖铺就的,日久天长,变得凸凹不平,那斑驳的痕迹,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井旁边有一棵老柳树。前来挑水的人们可以先不忙着打水,坐在绿荫下,吹着清凉的风,卷上一只旱烟,悠闲地拉一会儿呱,借此机会逗逗乐,说说话。每天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勤快的人们便一个个挑着水桶,来到井台上。吱吱呀呀的扁担声,叮叮当当的水桶声,以及人们的说笑声,将黎明唤醒,将村庄唤醒。几声清脆的鸟鸣,伴着袅袅炊烟,在村子的上空飘荡。忙绿的一天开始了。
挑水是个力气活,大多数是男人们的事情。小时候父亲在外上班,母亲既忙里又忙外,本来就体弱多病,因此街坊邻居们经常帮我们家挑水。母亲总是教育我们要记住别人的好,不要忘恩。可是日子是天天过,水要不断地挑,为了不愿给邻里乡亲添麻烦,我稍大一点就学着去挑水。
沿着湾边那条小路,我用父亲自制的那副扁担,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先用一根长长的井绳把桶吸下去,然后再左右一摇一摆晃动水桶,为的是好让水桶下沉。看到水快满的时候,就慢慢往上拉。因为力气小,每次都只能担不满的两桶。待我摇摇晃晃地双手托着扁担往回走,别人都会取笑我像银环,回到家时,两只桶里都只剩半桶水了。
乡亲们都很善良,怜惜我们母女,说什么也不让我去挑水。尤其是安东叔叔和他的弟弟安友叔叔,不管刮风下雨,一直坚持为我们家挑水。两家关系处得非常好,安友叔叔从小瞎了一只眼,人老实又能干,但老大不小了,却一直没有讨得一房媳妇。他不仅帮我们家挑水,还帮我们干些零碎活,母亲经常留他在家吃饭。吃饭的时候,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那些故事多数都是些鬼故事,每回听起来晚上都吓得不敢出门,但还愿意听,非缠着他讲完不可。
等我工作后,在供销社上班,因为深知农村柴油煤油奇缺,每次回家我都给安东叔叔捎回一些来,他非常高兴。安友叔叔后来也找了个邻村的弱智女人,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可惜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不幸患上了癌症,我去看他时,他半是感慨,半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想起他那么的好来,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怎么好人却如此短命呢?老天有时真是不公。他去世后,两个孩子由亲戚抚养,傻媳妇也回到了娘家,但她几乎天天都跑回来,在大门紧锁的门槛上,一坐就是大半天,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叫人心酸,谁见了,都忍不住摇摇头,轻叹一声。
乡村里的人们都是善良淳朴的,相互之间没有芥蒂,无论谁家有事都会热情地伸出援手,而且不求回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小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也为我的人生之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懂得了一些做人的根本,心存善念,知恩感恩,与人为善,无愧于心。
村里有一个老单身汉,是村里的五保户,没有房子,村干部就让他住在生产队的一间仓库里。他人非常老实,说话结巴,有点木纳。但心地善良,无论谁家有活,他都爱去帮忙,几乎家家都去过,深受大家喜欢。乡亲们对他也是关爱有加,每次干完活,都会特意做些好吃的给他,知道他一个人吃不好,谁家改善伙食了,就会特意给他送过去。母亲每次都是这样,做好了饭,就差我去送,我是很乐意去的。
他有个毛病,一个人回到家时,叼一只旱烟袋,巴哒巴哒地抽着,嘴里念念有词。我们总以为他很傻,为什么自己和自己说话啊,所以经常偷偷趴到他窗前听,听了以后就嘻嘻呵呵的笑,他似乎并不在意,继续在那里自言自语。
就这样,他除了干生产队的活,就是帮别人家干活,一直到干不动为止。活到八十多岁了,最后生活不能自理,又没有亲人,多亏了乡里乡亲们送衣送饭,嘘寒问暖。百年后,亦是乡亲们把他厚葬了。
我对门的一对百岁老人,是村里年龄最高的老寿星。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老奶奶就是个小脚老太太,长得慈眉善目,性情温顺,二老一辈子不温不火地过日子,五世同堂。生活简单清淡,最喜欢喝玉米粥,是用大锅柴火熬的,每天如此,雷打不动,一屋子的温温软软。或许,这才是生活的原滋味吧。
每次走在小时候无数次走过的田间小路上,感慨万千。路边的小草,依旧是那么碧绿,有蝴蝶在一朵野花前飞来飞去,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从前。过去是什么呢,天高云淡,岁月无边。
如今,我的村庄越来越好了,可是它越来越老了。父母不在了,优雅的四奶奶早就走了,安东叔叔,安友叔叔也相继离去,还有那些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给过我温暖和关爱的父老乡们,他们一个个地老了,走了。
那条曾经雨天两脚泥泞,晴天尘土飞扬的土路,如今也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路边安上了路灯,修建了娱乐场,置办了健身器材,人们在劳动之余,打球、唱歌、跳广场舞。老屋多数拆除了,换成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看到家乡的这些巨变,我不知是喜是悲,不知该喜该悲……
那个曾经给过我无数快乐的池塘,也被填平了一半,还有那几棵老枣树,早已不见了影踪。只有那口老井,依然默默地守护在那里,像是守家的老人,无声地看着家乡的巨变。只怕有一天,它也会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线,再也看不到它曾经的喧嚣和热闹了。
家乡是魂牵梦绕的地方,家乡是安放灵魂的原乡,家乡是游子的念念不忘。那些儿时温暖的回忆,那些快乐的时光,总是在梦里飘荡。当时只道是寻常,隔着岁月的烟雨回望,一半甜蜜,一半忧伤。时光催老了容颜,唯一不能改变的是,那一缕淡淡的乡愁,那一抹浓浓的眷恋,将永远烙印在心灵的最深处。
我的家乡,我的父老乡亲,我多么地希望,你能在我的文字里,在我的梦里,重新活一回!
——摘自莲韵美文集《等你,是一树花开》
莲韵,原名崔爱华,山东省作协会员,美文作家。著有文集《做一朵凡花,优雅独芳华》《等你,是一树花开》《向美而行》。作品发表在《山东文学》《齐鲁晚报》《劳动时报》《当代文学》《当代青年》,以及《陕西工人报》《德州日报》和《德州晚报》上。
德州日报全媒体出品
来源 | 莲香清韵
编辑 | 李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