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十五看大戏
□王凤华
小时候,每当过完年,母亲都会带着我去给姥娘拜年,然后再去邻村儿给母亲的婶子拜年,我称她二姥娘。二姥娘家有个梅姨,梅姨长得很美,在她村子里数一数二。记忆中身材匀称的她爱穿一件碎花儿的棉袄,大大的眼睛水灵灵的含着笑,一条长长的麻花辫儿垂在腰以下,她身上总有一缕淡淡的、清香的雪花膏味儿。

梅姨很喜欢我,每年都要留我在她家住一段时间,我也乐意留下来,一是因为喜欢梅姨,二是因为每年到了正月十五,梅姨家所在的“三堤口”就会搭戏台、唱大戏。
当走亲访友的拜完了年,当过年的新衣还依旧鲜亮,当鞭炮和二踢脚还不时远远近近地响起,当农家大门上的福字、春联和灯笼还依旧火红的时候,二姥娘家门外的一大片空地上就搭起了戏台。
小商贩们也赶来凑热闹,卖糖葫芦的、卖甘蔗的、卖荸荠、卖菱角的、卖洋茄子的……小孩子们的最爱是缠吹糖,吹糖是一种姜黄色的糖稀,用两根细棉柴棍儿挑起,上下左右缠绕,每缠绕一次还要往两边一拉伸,直到最后缠成有点硬的乳白色接近固态的形状,便一口填进嘴里,有点黏牙,甜中带香,吃了还想再吃。
戏台上的胡琴儿还在调着音,台下年轻媳妇怀里抱着的红脸蛋儿的娃儿喜笑颜开;眉清目秀的大姑娘们衣着利落、粉面桃花,三三两两的在一边小声地说着话;婶子大娘们的发髻梳得一丝不乱,手里还不忘拿着针线,几个人凑到一起,一边说笑着拉着家常,还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纳着鞋底儿;中年汉子让娃儿骑在肩上;小脚的老太太也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出来了;裹着白头巾的老汉们三五成群儿,抽一口自己卷的旱烟,笑眯眯地,高声谈论着往年的收成和来年的年景。
我们这些扎着羊角辫儿的小女孩儿,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或者半截儿甘蔗,在大人们中间嬉闹、追逐、穿梭,无拘无束的笑声在扬起的尘土里飞扬。
戏台上的锣鼓家什儿终于响起来了,轻重缓急、有板有眼。演出的剧目都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有河北梆子《大登殿》、吕剧《李二嫂改嫁》……在豫剧《穆桂英挂帅》里,穆桂英头戴金冠,身插彩旗,威风凛凛,杨宗保手持长枪上下翻飞,一招一式,英气逼人。在评剧《刘巧儿》中,梅姨演巧儿,梅姨扮相美唱腔好,台下的观众不停地叫好,至今我还记得她在戏中挎着小竹筐去生产队交棉线的场景。
乡村的大戏从正月十五一直唱到二月二龙抬头。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里,戏台是农村百姓文化和精神的舞台,是乡亲们联络感情的纽带,是我们幼小的心灵吸收乡土文艺的土壤。
我自外出上学到工作,直到今天,已多年没去过二姥娘家,梅姨嫁到他乡,也已多年未见。心里常常想念梅姨,脑子里也总会响起开戏前锣鼓家什儿铿锵的鼓点儿。不知道今年的正月十五,“三堤口”是不是还和我小时候一样,在姥娘门前的大块空地上,热热闹闹地唱大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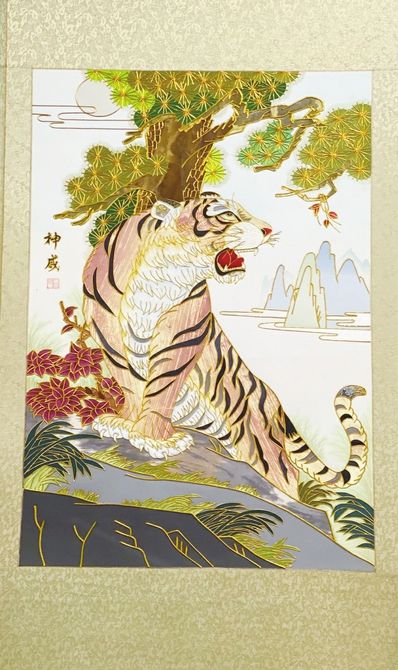
正月十五
灯笼、福字、窗花依旧火红
延续着新年的喜庆
家人的欢声笑语伴着年的尾声
汤圆,是团聚的符号和引子
唇齿间的甜糯、黏连
再一次将一家人的心紧紧相连
这一天也是团聚和分别的分界线
从此又是山南海北、相隔一方
母亲的目光里多了几分不舍
父亲的话语里多了几分沉默
屋门上的福字
从喜悦变成了等待和叮咛
大门上的灯笼
从欢庆变成了张望和送行
(作者简介:王凤华:德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喜欢读书,热爱文字。)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