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二哥
□邓吉收
随着“八一”的临近,对二哥的怀念越发浓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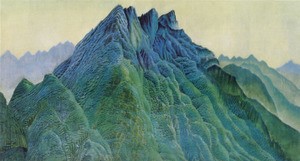
2022年7月28日,我二哥因病不幸去世,享年75岁。在人们寿命普遍提高的今天,这个岁数实在是说不上长寿,用我大哥的话说,属于不长不短的寿命。
在我的印象里,二哥身体一向是棒棒的,这或许与他当兵的经历有关。1969年,他从省内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当兵去边疆,在部队一干就是16年,直到1985年,才从部队转业到德州市一棉麻单位工作。
我在同胞五兄弟中最小,二哥大我15岁,在我只有6岁时,他就去当兵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兄弟俩见面极少。他在空军部队服役,每次寄回家的信,四个边沿都是红蓝条纹相间的航空信封,所以,娘常自豪地说,你二哥是开飞机的。
于是,我们只要一看见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娘就兴奋地冲我说,你二哥在上面呢。于是,我和侄儿们,就仰望着空中渐渐远去的飞机,情不自禁地哼起那广为流传的童谣:“飞机飞机你下来,我上去,我跟美国鬼子干仗去。”
至于二哥在部队服役的16年里,具体干啥,干得咋样,只听他说过做后勤工作,别的就一概不知了。整理他遗物时,据我所看到的部分奖章和证书,足以断定那16年里他是有成绩的。如“学雷锋先进个人”立功受奖证书,以及二等功和三等功的奖状,再如《转业军人证明书》职务一栏里所填写的副营长一职等。
二哥向来做事低调。他曾参加了边疆保卫战,并获得金质奖章一枚,还附带有两件都写有“中央慰问团”字样的慰问品:一件是白瓷茶缸,看上去仍白亮如新;另一件是白色毛巾。不知为啥,像参战这样的大事,他却一直守口如瓶,从未向家人提及过。若不是整理遗物看到奖章和慰问品,我们也许会永远蒙在鼓里。
二哥尽力践行忠孝。都说忠孝不能两全,二哥也不例外。在部队的16年里,回家探亲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平时,家里人和他的联系只能依靠书信。1976年,父亲去世后,家里立即给他发了加急电报。几天后,家里没见到他人回来,却收到了一封加急航空信件。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厚厚一打折叠整齐的冥纸。可以想象,当他得知父亲病故而不能回家奔丧时,内心是多么痛苦而又无奈呀。
为了尽孝,几年后的一个深冬,二哥回家来把母亲接到了部队,并在那里让母亲度过了春节。也许,他是想借此弥补由父亲病故所带来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吧。
二哥一贯心思缜密。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由于我们家里人多,不光吃饭是问题,手工缝制衣物也很头疼。他为了照顾一大家子人的生计,不光省吃俭用往家里寄钱,还在边疆想法子购买了一台“华南”牌缝纫机,通过火车托运回来。自从家里有了这台缝纫机,一家人缝制衣物方便了许多。他自转业到德州后,离家乡近了,回家乡的次数也就多了。母亲在世时,逢年过节,或遇晚辈结亲、完婚都要回来。
二哥待人淳朴。他每次回家乡,从不装腔作势,一言一行总是让人感觉那么亲近。见到父老乡亲,总是主动走过去,亲热得不得了。若遇到老人,就拉着对方的手,嘘寒问暖,问长问短。为此,邻里街坊的长辈见了他,总是叫着他的乳名说:“你在南方待了这么多年,咋口音一点也没变呀!”
二哥工作起来更是拼命三郎。他自转业到德州棉麻部门工作后,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这二嫂没少埋怨他:你二哥天天在单位忙得团团转,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家务活一点也指望不上他。
汗水从来没有白流的。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他后来挑起了单位重担——担任了经理一职。在那棉麻经济红火的年月里,一直有亲戚朋友上门找他“办事”,由于他原则性强,都婉转回绝。记得一位表哥曾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你二哥一点事儿也办不了。都啥年代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这就是我的二哥,在国与家之间,他选择笃志报国;在公与私两者,他秉持一心为公。
2021年“七一”前夕,他荣获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一枚。为此他兴奋不已,爱不释手,还通过微信转发图片告诉我。
哪知一向身体康健的他,此后却一病不起,不久就溘然离世。在向他遗体告别的人群中,既有他的生前街坊、同事、战友,也有社会朋友。面对他安详且明显消瘦的遗容,有人禁不住流下热泪。
人生苦短,心安即是归处。他生前荣获的各种奖章、奖状和证书,还有那送别的人流,就是对他一生最好诠释。我想,二哥若是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二哥,我永远想念你。

作者简介:邓吉收,临邑人,1981年参加工作。大专学历,中文专业,高级教师。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德州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省、市、县等报刊或融媒平台。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