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家
□王培惠
我明知道老家迁移到镇驻地去了,可偏偏恋恋不舍那老地方,这天下午,我欣然驱车回“家”看看。
对“家”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长年在外的人对“家”有种特别的怀念,有种割舍不了的情,那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尽管我小时候回家,少年离家,在家仅住四年的时间,但几十年来,总有一根无形的线连着,也许是血脉的缘故吧,藕虽断,丝还连。
我的“家”原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这儿鸟语花香,人杰地灵,五谷丰登。济邯铁路穿村而过,津浦铁路近在咫尺,紧傍赵牛河,离黄河不远。
村志记载是清朝年间从山东诸城迁徙而来。据说当时迁来时仅兄弟二人,几百年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现近千人,同宗的王姓还有在济南、禹城等地居住,都是从王楼迁出去的。前几年,济南的家人们来探望老家,我有幸和他们欢聚一堂,地点在晏城大酒店。时光如梭,光阴荏苒,几经变迁,村里现大部是王姓。有几家外姓也是在亲戚门上落户,也是有血缘关系的,早已融为一家人。
据传:当年,先祖兄弟俩使用一辆木轮千斤牛小推车,带着行囊,载着食粮。风尘仆仆地在空旷无垠的大地上艰难地行走,当时是天灾之后,荒无人烟,千里萧条,杂草丛生,虫蛇遍地,野兽出没,没有路径。两人已累得汗流浃背,筋疲力竭。再继续走,就是古时候发配朝廷钦犯的不毛之地。就在太阳快落山之时,红彤彤的太阳映照大地,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儿,微风习习,俩人欲停下歇息。回头仰望那黛色的泰山,高耸入云,巍峨壮观;眺望那蜿蜒九曲的黄河,汹涌澎湃,涛涛万里。这儿离山不远,傍水咫尺。不正是风水宝地吗?正思间,一对凤凰飘然落在眼前一棵大树上,这更坚定了兄弟俩留下来的信心。
从此,兄弟俩在此安营扎寨,建屋垦荒。后辈们在凤凰栖息的地方建了一座三层楼,曰“王楼”。我小时候曾见过这楼的砖,是蓝色正方形的,边长约30厘米,厚约8厘米,重约4公斤。
我下车顺着原街行走,思绪万千,感慨万分。我首先想起我的爷爷,他的名字是王玉安,那可是一条汉子,胳膊上能跑马,拳头上能站人。爷爷的公职是医生,“行医时,鞠躬一生,不求闻达,但求利人,浩然正气,刚直不阿。”爷爷对《易经》也很有研究,本族现使用的家谱也是出自他的手,现记载于村志,是“庆、元、长、春、和、茂、盛、德、勤、学”十辈。另外,爷爷的毛笔小楷写得也非常漂亮,苍劲有力,他誊写的“千金方”我至今保存。
爷爷在医院退休后,88岁时依然步行出诊,擅长妇科,疑难杂症,针灸技术尤佳。在我仅几岁时曾教我学习一些医学知识,如眼睛、鼻子、嘴上火,就是思虑过多,心肾不合,虚火上升。还说过:白糖、冰糖是寒物,红糖为热物等。可爷爷不幸就在88岁那年病故,留下了终生遗憾,我再也没有机会学习医学了。爷爷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那一刻的记忆中。只有在梦中相见了。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默默地在爷爷的坟前焚香烧纸,寄托哀思之情。
我站在“家”的原址上,那棵大榆树、老枣树处,脑中浮现出母亲的形象,我在外地读书、工作,每次回家,母亲接我送我的情景历历在目。母亲晚年患高血压、冠心病,拄着拐杖,步履蹒跚,满头银发。每次都望眼欲穿地等我。我走时,又是那么恋恋不舍,目送我走得很远。我偷偷回头,让我潸然泪下。我想:每一个做母亲的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吧?这就是伟大母亲的特性。
母亲是1980年离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干部”),享处级待遇。母亲出生在省城大户人家,家就在趵突泉不远处,有家族企业,是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宋家。母亲放弃优渥的环境,从一名省城的大家闺秀走向革命道路,当年仅十几岁便从军。
母亲对我家贡献最大,对我的影响也最深。谆谆教诲我要学有所长,要有责任心,要有担当,要有忧患意识,“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五技穷,不如一招鲜。”“人要实,火要虚”等。这些言辞至今依然如雷贯耳,让我受益匪浅,也成了我教育子孙的教科书和座右铭。我下岗后的生存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多亏有一技之长。
我沿原大街行走,记得这里曾是石碾,那里曾是石磨,我们在这儿打过尜尜,踢过“房子”,玩过铁环,仿佛就在昨天……最让我忘不掉的是那口甜水井,小时候曾亲自趴在井沿上往下看。高高的台子上铺着大板石。井口直径有一米多,井深有七八米,井下直径有二三米,有几个大喷泉,不断涌出清洁的水。甜水井紧靠一大水湾,斜对着学校,我们读小学时没少喝这井里的水。水清甘洌,沁人心脾。都说这水脉系泰山,源自黄河,后来,我亲自化验过这水的指标,钙镁含量低,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物质。达到优质泉水标准。这口井几百年来养育了我的父老乡亲,应该说是有大恩大德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家乡的水井》,发表在刊物上,就是为报答这口井之恩。
走到母校原址处,更令人感慨万千,小时候我赌气任性,不爱读书,11岁了还在家喂猪喂羊,后来只好插班直接读四年级,现在回想起来,后悔不已。真的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多亏遇见一些好老师,自己也知耻而后勇,直到以后在同行业考试,县、地、省得了一二名,自己的小说、散文也在全国发表,心里才略有一丝欣慰。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看似不起眼的农村学校,竟培养出厅、县、局干部,还有教授、专家、律师、工程师、作家、书法家、画家等,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吾引为自豪和骄傲,难怪凤凰偏佑此地。
如今,我为了不和老家断线,又要了一套楼。留住的不仅是楼房,更是一片心思。我知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道理。我虽不成材,但愿做一片绿叶,也得美化家乡。更愿家乡的天湛蓝,云洁白,水清澈,空气清新。上风、上水、上家乡,为子孙留下一片天地。
我漫步在松软的土地上,朝北望去,离此不远,那是一片坟冢,是祖先歇息的地方。此刻,我有千言万语要说,也难以用拙笔记录下这非常时刻。家永远是遮风挡雨的港湾,当累了时是歇息的地方,是父老乡亲们交流感情的处所。
落日熔金,霞光万道,我打断遐思,无奈难舍地望着这片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的热土,心里默念:我会记住这里的一切一切的,我会再来看你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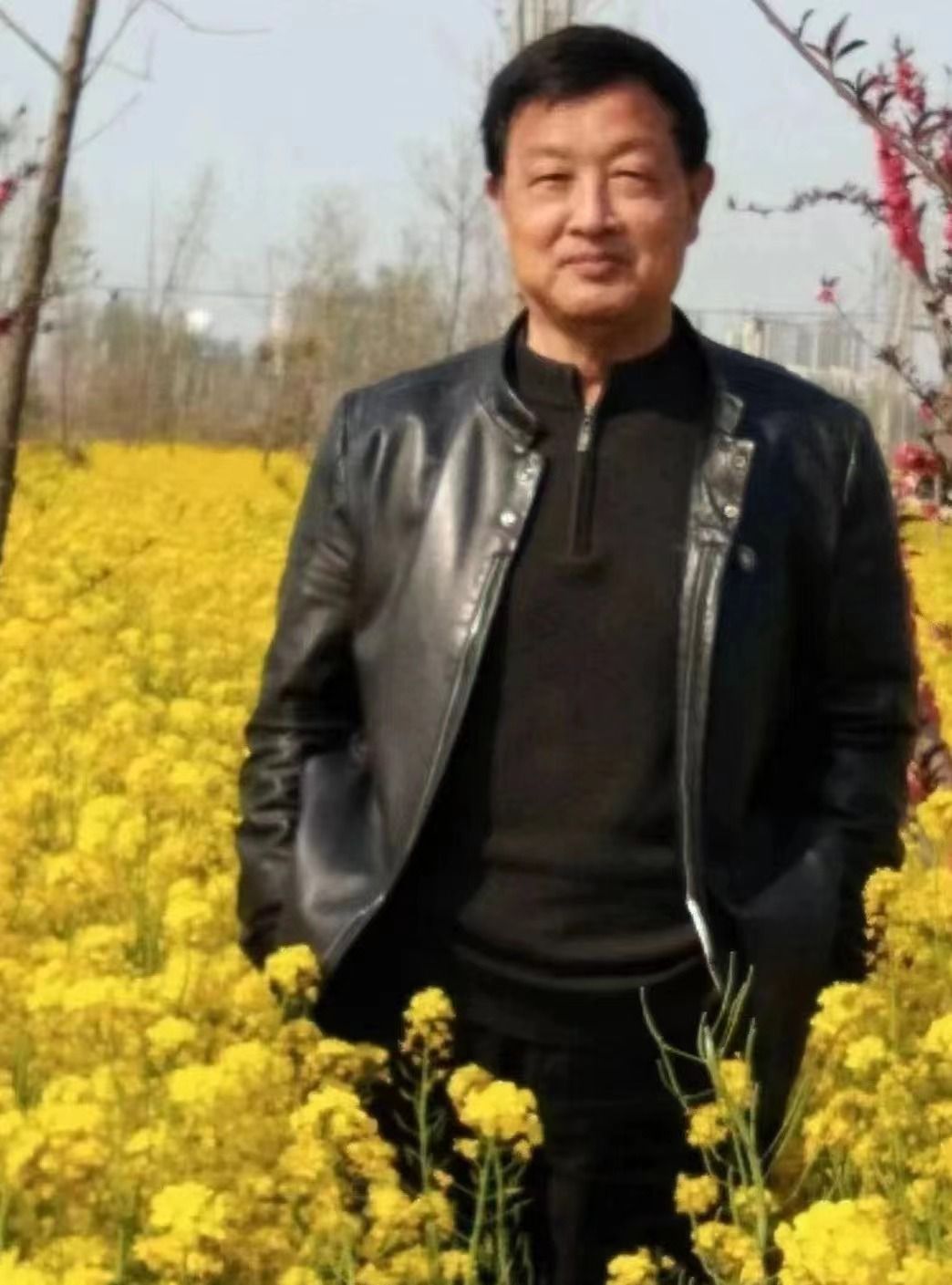
作者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