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大学梦
□张永生
每个学生的成长轨迹都是独特的。从入学开始,我们都怀揣梦想,希望通过年复一年的努力,不断升级、考上理想的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多数人正常的人生轨迹。当然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每人既心怀理想,又要面对现实,在求学的每个阶段,会不由自主地作出一些别样的选择。我就是这样,因为没有读过高中,失去了直接进入大学读书的机会,以致参加工作后,始终对庄严神秘的大学校园充满向往,希望能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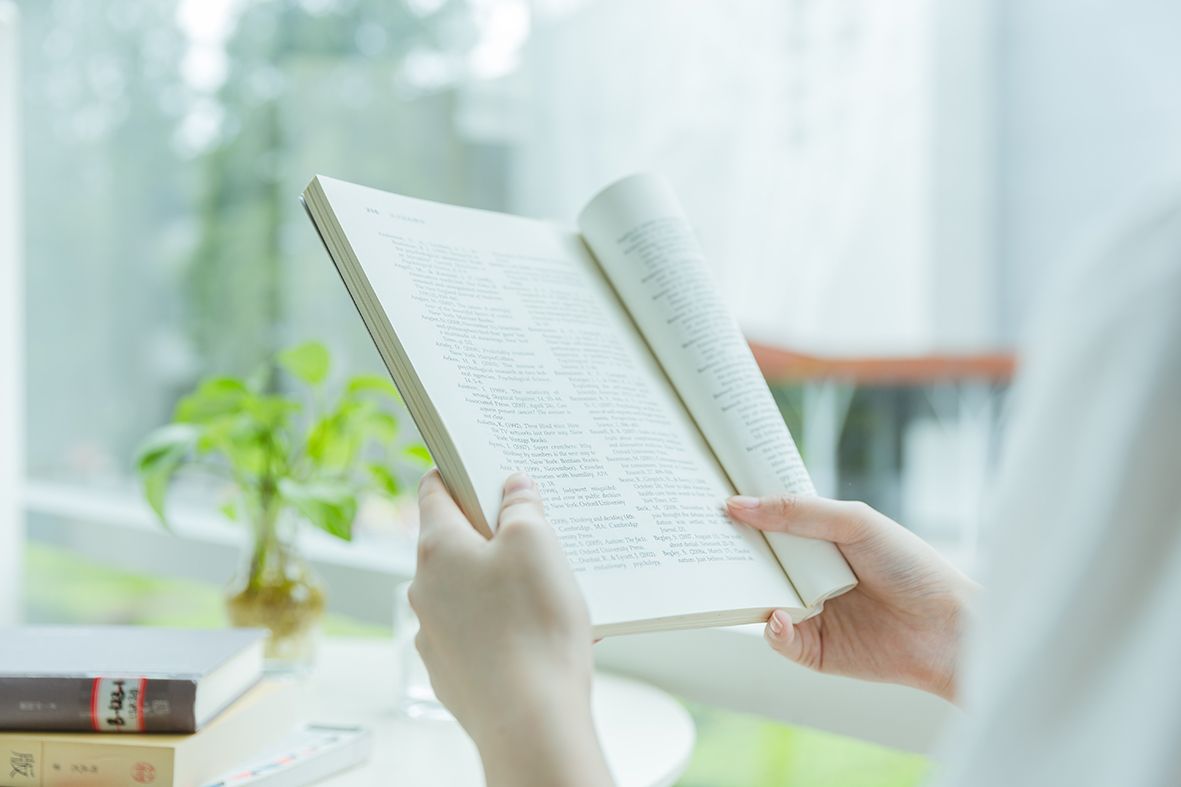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农村孩子,上学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跳出农门,摆脱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过上城里人的生活。1981年初夏我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填报志愿面临高中和中专两种选择,考上高中,三年后再上大学,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理想愿景;而考中专,则能跳出农门、改变身份,而且能给尚不富裕的家庭减轻负担。这是当时多数农村学生最直接、最现实的梦想。当时县里的政策是中考共录取500人:前200名入重点高中,中段100名录中专,后200名进普通高中。在那个择优录取、录取率较低的年代,考上重点高中,经过三年努力,再考大学应该很有希望;若上普通高中再考大学,能否被录取则有很大不确定性,而且高中三年还要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所以多数农村学生从实际出发,还是奔着中专的目标而努力。比较幸运的是,成绩公布后,我被一家师范学校录取,父母非常满意,同时也引来很多同学的羡慕。我高兴的同时,也因为上不了大学而感到有点不甘和无奈。
师范三年,毕业之际,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初中中师毕业生(之前两年分别是高中和民办教师班),我有幸赶上了留校工作、推荐上大学、选调进机关等多个机会。这些机遇令近二百名面临毕业分配的同学趋之若鹜。审视当时的自身条件,我最盼望的还是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大学继续深造,实现少年时期的心中梦想。我在毕业之际加入党组织,后又经过推荐考察和层层选拔,作为选调生进入当时的德州地委所属一家机关单位工作。虽与上大学失之交臂,但是全家都非常高兴。
参加工作后,我努力适应新岗位,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文化学习,盼望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想。多年后,我还常常梦见考上正规大学了,梦醒之后总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失意。甚至每当看到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特别是涉及大三、大四生活的内容时,都会产生一种“羡慕嫉妒恨”的负面情绪。随着干部“四化”政策的推行,机关干部的提拔越来越重视学历,尽管我经过不懈努力,先后完成了业余大学(在职半脱产专科)和省委党校(函授本科)的进修学习,知识层次的提升也对工作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从内心讲,仍盼望能够进入正规大学学习深造,特别是有段时期成人高考毕业生能力一度受到质疑,干部提拔任用上也是更加注重全日制大学学历,这让我的大学梦想更加强烈。
1999年,市委为培养年轻干部,作出了在市直机关选派部分优秀年轻干部,进入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时称“三南”)研修的决定。这对于当时符合条件的市直年轻干部来讲,无疑具有很大诱惑力,每人都盼望能赢得机会,同时也再次点燃了我圆梦大学的激情与梦想。通过单位推荐和统一考试,我于2000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研修学习,真正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大学梦。
进入南开大学,多少次魂牵梦绕的高等学府就这么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名校的学术声誉、前沿的科研成果、顶尖的师资力量、勤勉的莘莘学子,连同那林荫掩映的校园、窗明几净的教室,都让我眼界大开、兴奋不已。置身其中,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我们这批学员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宝贵时光,大家课堂认真听讲,课下交流研讨,聆听各种讲座,外出参观学习,精心准备论文、分组进行答辩,一年的研修生活丰富而充实。在扎实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我还承担了班里的编发校刊专版、起草总结材料等班务工作,结业论文获得了95分的班里最高分,并且作为学员代表,在结业式上作了发言,的确收获颇丰,不虚此行。
这些年来,回顾走过的路,我始终坚信,每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特别是对于年轻机关干部来讲,个人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党的好政策,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和培养,离不开孜孜以求不懈进取的恒心和毅力。我们应该以感恩之心敬畏职责、不懈学习,用心用情回报组织、不负人民,这样的人生方能愈发丰盈饱满,在充实中彰显生命的意义。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