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娃记
□刘志宇
虽然早在知道妻子怀孕的那一刻,我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当儿子真正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还是被一种巨大的惊喜和莫名的感动充斥了整个身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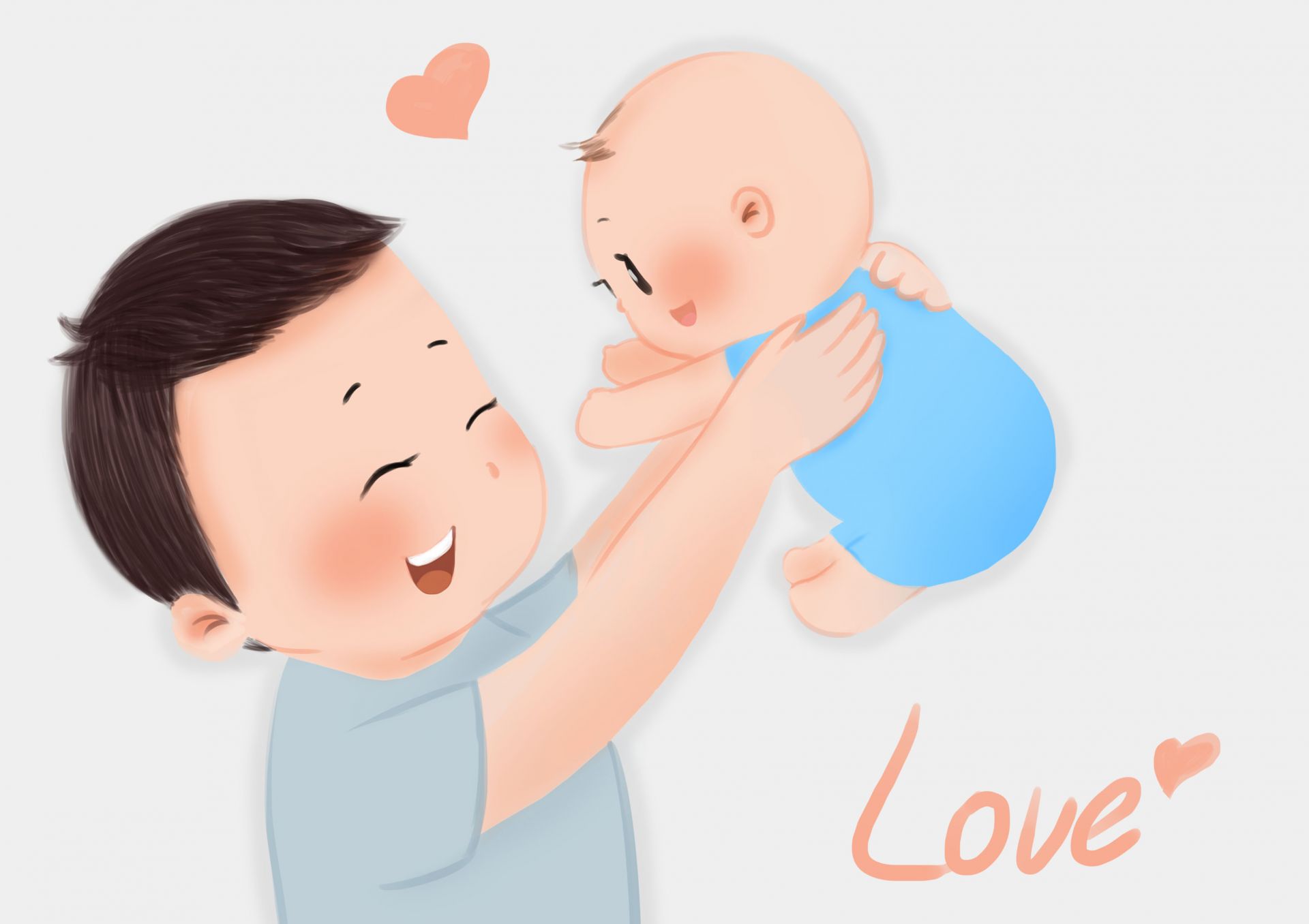
细数这三百多个日夜,妻子的蜕变历历在目。曾经轻盈灵动的身影,渐渐化作孕晚期步履迟缓的模样;曾经天真烂漫的少女,眼中开始闪烁温柔坚毅的母性光芒。
而在待产室,她亦是用自己的身躯化作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桥梁,用自己的坚韧和勇敢迎接着儿子的到来。
产房外,四位爸爸妈妈的焦急与担心,自己时刻湿润的眼眶,所有焦灼与期待最终都化作新生命降临的曙光。
就这样,儿子就在早已预料与突如其来的交织中诞生了。
当护士抱着襁褓走向我时,我竟顾不上细看儿子的小脸,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媳妇还好吗?”直到确认妻子平安,才颤抖着接过这个柔软的小生命。
初为人父的我,不懂得怎么正确地拥抱他,更不懂得他的哭声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产前看的每一个育儿小视频、每一条喂养小知识,在此刻都变成了手足无措的慌乱。
还在医院的那几天到底发生过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尽管身子虚弱却依然要喂养儿子的妻子;不管白天多困倦,却依然坚持晚上守在这里的母亲和岳母;询问我们想吃什么,坚持要自己做并且按时送来的父亲和岳父。
生娃后的日子,乍看似乎没什么不同:太阳依旧朝升暮落,生活依旧是一日三餐的烟火气,我也仍在祖祖辈辈扎根的小城里,看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可心底总归是多了一丝牵念,让一切又悄悄换了模样。下班后,不再琢磨着约朋友去哪里驱散工作的倦意,反倒归心似箭,只想快点回家抱抱娃;购物软件的推送栏里,文玩、手办早已淡出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牙胶、点读本这些婴儿用品;夜晚再难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常常是清醒地望着窗外,看天空从墨蓝一点点泛起鱼肚白;就连刷抖音,关注列表也从“听风的蚕”换成了“崔玉涛”。
若说成为丈夫是扛起了一份责任,那么当父亲之后,我更想成为整个家最安稳的港湾。
生活依旧在驱使着我往前走,当看到母亲和岳母抱着孩子,目光里盛满小心翼翼的疼爱时,《陈情表》里那句“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突然在脑海里翻涌。从前读来只觉文字恳切,如今亲眼看见两代人对这个小生命的呵护,才猛然懂了那份血脉相连的羁绊——她们抱着的是我的儿子,更是延续了半生的爱与牵挂。
又想起给学生讲过的《背影》。那时台下的孩子多半不懂,看得出只是为了附和站在讲台上的我,这跟我上学的时候又何其相似。
我便说:“这篇文章要分两个时候读。第一遍,上大学或者第一次远离父母时读,品的是父亲送站时的欲言又止。第二遍,等你们为人父母了再读。”接着,我顿了顿,“当然我现在也没到读第二遍的境界。”然后便是和学生一起的开怀大笑。
如果你问我现在读来是什么感触?那我会告诉你,原来当年月台的台阶并不难爬,一切不过是父亲再寻常不过的动作;橘子也从来不是橘子,不过是一个父亲想着“这果子甜,要给我儿尝尝”的寻常心意。父母之爱从来不是沉重的山,而是一缕缕温柔的风,从祖辈吹到父辈,再轻轻落在下一代的襁褓里。
曾经的我总觉得“丁克”是自由的终极答案——怀孕时的小心谨慎,产后凌晨三点被啼哭撕碎的睡眠,余额在奶粉尿布间的窘迫,连和朋友聚餐都要算着回家喂奶的时间……那些被琐碎切割的生活,曾让“不生娃”成了许多年轻人最理直气壮的选择。
可当某天襁褓里的小人突然用没长牙的嘴咧开笑,奶香味的小脑袋往颈窝蹭时,才惊觉那些被偷走的自由竟变成了另一种圆满:凌晨换尿布时他突然抓住你手指的温热,努力抬头打量这个世界的惊奇——原来生命的传承从不是负重前行,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心动,把所有“兵荒马乱”都酿成了甜。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看娃?
曾经的我会告诉你,看娃不过是奶粉、尿不湿罢了,是看着他成长,陪着他长大而已。
但现在的我才堪堪懂得,所谓看娃,是将生命切割成以孩子为刻度的时光碎片,是无数个被啼哭揉碎的漫漫长夜,更是从此把心化作风筝线,无论行至天涯海角,都系着那份跨越山海的牵挂与惦念。
敲击完最后一个字,指尖悬在键盘上的瞬间,忽然想起多年前在《读者》上读到的一则小故事。也顾不得是否贴合此刻的语境,姑且分享出来,权当这篇文字的收尾吧。
“男人的孩子出生了,他高兴地抱着孩子,不住地亲吻并且流下了泪水,对着孩子说了很多的话。他清楚地知道孩子流着他的血液,他对孩子有很大的期望,想竭尽所能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无条件地给孩子。这时,医院的一位老护工经过他的身边,指了指他年迈的父亲说:‘当初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父亲也是这样的……’”
作者简介:刘志宇,95后,山东武城人,中共党员,德州市作家协会、诗词协会会员。笔耕所得,偶见于《德州日报》《德州晚报》等报刊。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