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砺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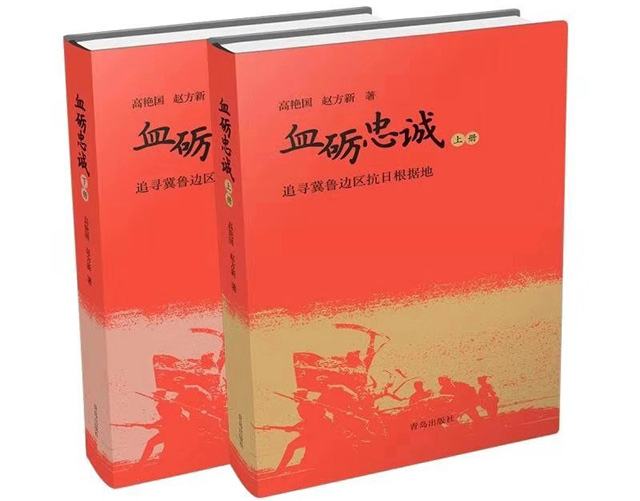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以无限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们!
第二章 冀鲁边前传
悲怆马颊河③
这位“农民”就是化装的刘格平,他一方面怒斥当局腐败无能,一方面又号召军警们站到人民群众一边来,不要帮着胡振国为虎作伥。许多军警面有愧色,低下了头。刘格平的讲演引发了群众的怒潮,大家高呼着:“停止挑河!”“释放胡恒熙、张笃骞!”“找傅奎升算账去!”……
胡振国见势不好,赶紧带着军警们骑上马,一溜烟回了县城。
刘格平鄙夷地瞧着胡振国一行的背影,这些纸老虎一遇到风吹雨打就露了馅儿。
群众高昂的情绪也感染了刘格平,他大声说:“乡亲们,胡恒熙、张笃骞为了反对挑河工,被反动官府抓走了,我们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吗?我们现在就去请愿,把他们保出来好不好?”
群众齐声答应着“好”。
刘格平大手一挥,带着邸玉栋、胡林晓等人跳下台,身后跟着上万群众,敲着锣打着鼓,高呼着口号,向着县城走去。刘格平让党员骑上车子,到沿途村庄继续发动群众,因此不断有人汇入这支洪流,到县城时队伍已发展到两万多人。
胡振国跑回城后,早已命令军警关闭了城门。庆云县城有东、西两个大门,东门包裹着厚厚的铁皮,西城门比较单薄。请愿队伍绕过东门来到西门。胡振国带领军警站在城墙上,气势汹汹,吹胡子瞪眼,高喊着:“反了,反了,这简直是造反了!”群众一起叫着:“开门!开门!”
胡振国欺骗群众说:“城门不能开!你们先退下去,可以派代表进城。”
群众都不答应,齐声回答:“我们都是代表!”
有人喊道:“别跟狗日的磨蹭了,我们砸开门!”
愤怒的人们用杠子撬,石头砸,最后用肩膀扛,几十个壮汉一起顶住城门,口里喊着号子:“嗨哟嗨——齐用力呀嘛嗨哟嗨——”城门慢慢松动,渐渐晃悠,二十多分钟后,轰然一声倒在地上。人们穿过尘土,潮水般涌进城来。有军警上来阻拦,被胡林晓等人卷过去下了枪支。胡振国和公安局局长率领军警跑下城楼,荷枪实弹对着夺枪的胡林晓等人,他们也呼啦一声推上子弹,与军警对峙起来。僵持了两三分钟,胡振国面对着眼中燃烧着怒火的人群打怵了,带着军警溜走了。
刘格平带领着请愿队伍直奔县衙,又有市民加入进来,汇成了一支两三万人的洪流。县衙大门紧闭,保安队和警察队在门前设置了防线,还在几个制高点架上了机枪,阴森森的枪口对着群众。这阵势给人一种一触即发的感觉,不少人被吓得往后退缩,胡林晓等共产党员排开众人冲到前边,继续往前走,后退的群众也随即跟了上来。他们堵住县衙的门,高呼着:“请县长出来!”“我们要求放人!”“停止河工!”……
县衙里没一个人敢露面。人潮开始冲击县衙大门。眼看大门就要被推倒了,这时里面走出一个圆脸、教员模样的人,哆哆嗦嗦地说:“我就是县长。”
其实他只是县政府的财政科科长,是替傅奎升出来“顶缸”的。
群众嚷叫着:“赶快放人!”
他急得脑门汗水涔涔,语无伦次地说:“不能放,不能放,你们先回去,一切再好好商量。”
群众骂道:“狗官放屁,俺们再也不能叫你们糊弄了,现在必须放人!”
胡林晓喊道:“他不放人,就砸他的监狱!”
监狱就在县衙的西边,大家拥到监狱门前,举起手里的家伙就要砸,公安局局长举起手里的枪,一脸哭丧相地哀求着:“不能砸啊!砸了连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我请示县长去。”
群众呼喊着:“不放人连县衙一块砸!”
反动当局迫于群众的压力,当场释放了胡恒熙、张笃骞二人。当二人走出监狱时,群众一拥而上,欢呼着将二人抛向空中……
随后胡恒熙、张笃骞被群众选为河工代表,同傅奎升一伙人直接谈判。傅奎升为形势所迫,最后在“具结文书”上签字。胡恒熙当众宣读道:“马颊河疏浚工程浩大,人民生活贫困,无力负担,准予不挑,立此为据。”傅奎升也到群众面前,结结巴巴地说:“河工不叫老百姓挑了,我负责向上呈报。”
人群如沸,欢呼胜利。
胡林晓等人立刻买来十五尺红布,制作成一面横匾,刘格平饱蘸浓墨,挥毫写下一行遒劲有力的大字:庆祝庆云县罢免河工斗争胜利!横匾用两根竹竿挑起,为了防风,还在大字中间剪出了一些小窟窿。就这样,兴奋的群众打着横匾,架着胡、张两位代表,高呼着口号开始了游行。
刘格平和胡恒熙并未被初步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当晚两人又召集众人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会议决定第二天由胡恒熙、张笃骞二人组织群众在板营镇集合,到马颊河工地游行;特委交通邸玉栋通知津南各县委的军事委员来开会,研究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
第二天,胡恒熙和张笃骞带领党员和群众在板营镇集合后,高呼着“庆祝罢河工胜利”“将罢河工斗争进行到底”“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冲进马颊河工地,向正在施工的群众宣传说:“河不挑了,县长已经具结签字画押了!”民工一听,无不欢呼雀跃,扔下铁锨,拆了工棚,加入队伍中来。
下午,游行队伍返回板营镇广场,准备再次开会庆祝。板营镇公安分局局长孙长荣指挥七八十个军警,挥着枪支恫吓群众,有意挑衅。孙长荣在当初催河工时,动辄鞭打脚踢群众,加上平日作恶多端,群众早已恨之入骨。
有人高喊:“惩办孙长荣!”
孙长荣吓得赶紧溜进了土围子,紧闭大门。群众不依不饶,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几下冲开了大门,涌进院子里,却怎么也找不到孙长荣。忽然,有人指着屋顶喊:“那不是孙长荣吗?”孙长荣在屋顶上吓得像只寒风中的小鸟瑟瑟发抖。城东大淀村的张云峰上去一棍子,将他打下房来,愤怒的群众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揪着他围着镇子转了一圈,这一圈下来,不知又被打了多少次,身上的黑色警服都被撕成了一条条飘带。胡恒熙见群众围殴孙长荣,几次制止无效,孙最后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生死未卜。有的人见惹下是非,有些惧怕。
胡恒熙为了安抚群众情绪,找到区长谈判,并立下字据,之后向群众宣布:“板营公安分局局长孙长荣手段残暴引起公愤,被群众打伤,生死存亡与群众无干,武器、物品均无损坏丢失。”他接着宣布,明天在严家务大集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积极参加。
第二天的严家务大集,为这次震动华北的马颊河罢工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接到报告后,连夜从沧县派出了一个骑兵连。刘格平、胡恒熙等人也已获知敌人将要镇压的情报,但他们知道这种时刻一旦退缩,将使群众丧失对我党的信心,所以宁可牺牲生命,也要跟敌人斗下去。
4月20日,严家务村里枪声不断,刘格平被敌人打断一根手指,胡林晓左臂被子弹洞穿,杨德然被打破了头,同时被捕的还有胡恒熙、胡泮河、张云峰、刘全禄、刘子亨、刘全政等人和八名群众,史称“四二〇血案”。
不久,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登载消息说,庆云县共党分子为河工肇事暴乱,经军警镇压已平息,共逮捕“共匪”十七名云云。
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监狱。
胡恒熙透过铁窗棂望着雨帘密织的院子,他身上的新旧创口阵阵发痒,监狱里几乎所有的刑罚都叫他尝遍了,他还是没吐露一点党的秘密,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与刘格平初次见面的那个日子,一次次重现于他的脑海,差不多已经十年的时光了,可是当时的情景却依然那么清晰。一路走来,从迷茫的青年到信念坚定的中年,他如同一块生铁淬炼成钢,不用说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受到他恢宏而渊深的气度。
一次他借上厕所的机会,靠近了关押刘格平的号房,刘格平也正在窗口饱含关切地盯着他,悄声问他:“胡,怎么样?”
他明白刘格平的意思:“没有什么!”
胡恒熙急速撩了一下上衣,呈现在刘格平面前的是半个被粗火香烧得红红黄黄的脊背,他的心都要炸了,怒火烧得他浑身战栗,几欲跌倒。
胡恒熙回来时又对他说了一句:“你放心,我一个字都不说。”
刘格平噙着泪水说:“好。”
没人知道胡恒熙最后的人生历程是如何走完的,只知道敌人确实从他的嘴里没抠出一个有用的字眼,他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却因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而害上严重的痢疾,不治身亡。
刘格平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44年4月获释出狱。
马颊河暴动失败后,庆云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骨干要么入狱,要么外逃。更严重的是,曾参加暴动的盐山县委组织部部长王连壁见革命陷于低潮,灰心丧气,被捕后变节,亲自为敌人引路搜捕地下党员,盐山和庆云两县的党组织和联络站几乎全部被破坏,津南地区的革命形势骤然坠入冰窟。
历史老人摆弄着一枚硬币,一面是光明正大的人格,一面是卑鄙无耻的私欲;一面是钢铁铸成的忠诚,一面是恬不知耻的背叛。而现实在这枚硬币上的投光则更为陆离斑驳,王连壁叛变革命,而他的弟弟王连芳其后却成了冀鲁边区回民支队的政委,并最终亲自判决二哥王连壁死刑。
马颊河恢复了平静,河滩上的野花迎风怒放,灌木丛也饱满起来,两岸的庄稼地堆金砌银地随季节流转着,美丽丰饶的冀鲁边平原默默承载着苦难和数不尽的悲欢,正蹒跚地走向她最激荡、最悲壮、最雄奇的历史时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