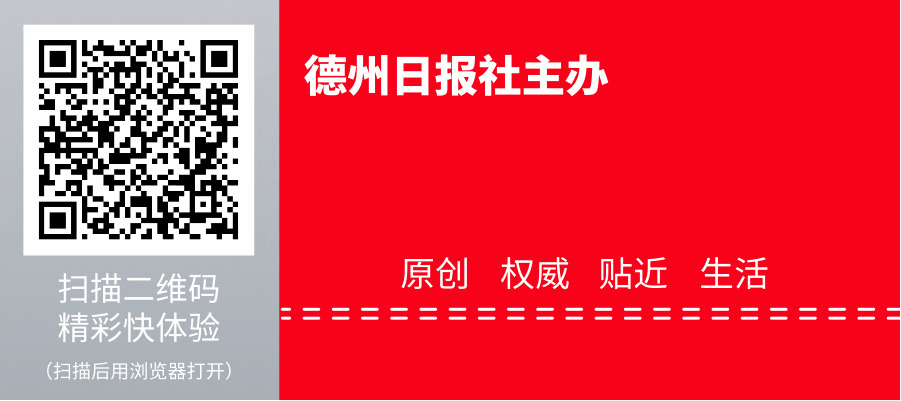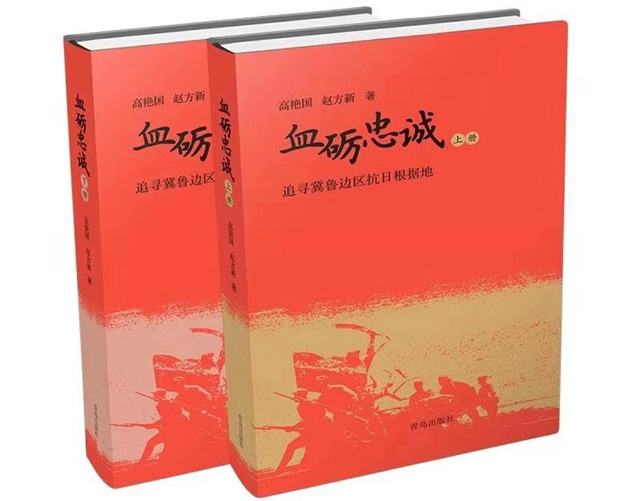
1939年4月1日,鲁北的原野已有怯怯的春意萌动。八路军挺进纵队五支队五团团长龙书金,同大多数人一样并未意识到巨大的凶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当时他的部队驻扎在陵县县城以东15里的大宗家村,前一天晚上,他跟团政委曾庆洪到距此二三里地的侯家村参加支队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气氛那么热烈,情绪那么饱满,令人几乎忘记了当下所处境况的困苦和危机,恍如一头撞进阳光灿烂、歌舞升平的桃花源,不知身处何世了……在以后的岁月里,龙书金经历了无数的苦战、恶战,但任何一次都没有这一次来得刻骨铭心,以致晚年的梦中每每从大宗家旱河的沙滩上醒来,浑身酸疼,惊魂无定。
那段日子确实值得五支队的每一个人欢欣鼓舞,胜利一个接一个,似乎这才是这支老牌八路军部队应该过的有尊严又有存在感的日子。
自日军回师华北以来,五支队主力奉命到鲁北一带活动,以陵县、临邑为中心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根据地。
这天支队长曾国华正带着队伍行军,一匹快马迎面疾驰而来,被警卫喝令拦下,滚鞍下来一人,简单说了几句,便在警卫的引领下踉踉跄跄地跑到曾国华面前,嘶哑着嗓子急火火地说道:“曾支队长,快、快、快救救我们吧!‘十八团’的老百姓遭、遭殃啦!我是副、副团长……”后来知道来的这个人是“十八团”的副团长王如玉。“十八团”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是陵县东部最大的地方武装民团,1920年始创于仓上村,原由18个村庄的民众组建起来,故称“十八团”。后来“十八团”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会员村达到200多个,控制了陵县东部和北部以及商河县西南部、临邑县北部,常备军只有200多人,但藏于民间的枪支有2000多支,团众平时务农,一有情况数千人持枪提刀上阵。五支队初入冀鲁边时,曾途经“十八团”的几个村子,其首领担心五支队趁机抢占地盘,组织团众武装封路阻止五支队。五支队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反复阐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最终得以和平通过。其后,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派出一批党员进入“十八团”,引导其顺应抗日救国的大势,“十八团”渐渐认同了共产党的主张。这次王如玉十万火急地前来求救是因为“十八团”遭到了陵县另一支民团武装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九旅于志良部的围剿,危在旦夕。
于志良是陵县于集人,他的队伍开始规模不大,后来他击垮了陵县神头镇李会亭的地主武装,占领了神头镇,兵力迅速扩大到2000多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势力范围向西延伸到德县地面,向南辐射到平原县境。1938年7月,沈鸿烈跑到神头镇,亲自委任于志良担任山东保安第九旅旅长兼陵县县长,此后其所作所为更加肆无忌惮。有资料说于志良是冀鲁边早期的共产党员,但他被沈鸿烈收编后甘心当马前卒,卖力反共,一点看不出“念旧”之意。他视陵县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又气恼于无法把手伸进“十八团”的地盘,所以一直处心积虑想解决掉这颗“眼中钉”。于志良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陵县本地乡绅许有然跟“十八团”团长郭仁山发生个人冲突,带着兄弟、儿子去仓上村团部挑衅,副团长王如玉勃然大怒,当场枪杀了许有然的三个兄弟。许有然遂往宁津大柳店找民团首领杨吉州哭诉,二人为至亲,杨吉州跟于志良是故交,三人一拍即合,决定讨伐“十八团”。同时,于志良又向驻陵县日军谎称“十八团”附近有八路军活动,日军也对“十八团”展开了攻击。“十八团”团长郭仁山先是带人依托土楼子对抗于志良的进攻,于志良见强攻不能立刻奏效,就花言巧语骗郭仁山说他可以“居中做调停人”。郭仁山轻信其言,走出土楼,被于志良逮住绞死。“十八团”的村庄被于部攻破,于志良下令部下“自由行动三天”,团丁们肆意妄为,烧杀淫掠,一点也不逊于日本人。
王如玉侥幸逃出,一路狂奔寻找五支队求援。
曾国华对正准备埋锅造饭的战士们下达了进攻令:“同志们,我们的乡亲们正在遭受土匪和日寇的洗劫,我们早一分钟到就能早救一些人,迟到一分钟,不知多少人家就要遭殃!现在我命令队伍以最快速度开往仓上村,消灭顽匪于志良和日寇!”
突然从天而降的八路军打了敌人一个猝不及防,刚刚还沉浸在抢劫掳掠的快意里的敌人,瞬间便成了八路军的瓮中之鳖,于志良部大部分人马和十几名日军被歼灭,于志良被活捉。
于志良民团也曾抗日有功,1938年,其与八路军配合围攻过陵县日军,又截击日军汽车,活捉17名日军士兵,还曾为阻止日军列车通过,在平原县境内破坏铁路六七里。又加之驻德平的曹振东出面为他求情,挺进纵队司令部希望他戴罪立功。没想到于志良竟以剪刀自杀,以此要挟八路军无条件释放他。最终于志良因民愤极大,在五支队召开的公审大会上被枪决。
“十八团”自愿被挺进纵队收编,同时陵县的另一支民团“二十二团”也主动要求收编,这样一举打开了整个陵县的局面,使其成为边区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尤其是陵县的三洄河村,党的群众基础厚实,人们私下都称之为“小莫斯科”。
1939年3月,五支队五团一营在营长谭端志指挥下,在陵县魏龙江村成功解救被日军围困的曹振东的国民党保安队第五旅,在战斗中谭端志不幸牺牲。其后,日军紧紧咬住五支队不放,五支队避其锋芒,巧妙周旋几天后,重返陵县县城以东的前后侯家、大宗家、阎富楼、赵玉枝家等村进行休整。
无疑,五支队在陵县的高调出没,引起了日军方面的注意,其加强了相应的情报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曾国华中将在《思想历史自传》中沉痛地写道:“1939年春,敌攻占武汉后,回师‘扫荡’敌后,边区的斗争从此紧张起来,‘扫荡’逐渐频繁,部队进入了日日夜夜的战斗环境中。由于正确地运用了游击战术,所以反‘扫荡’不断取得胜利。此后自己和部队则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轻敌麻痹思想,因之,造成一次严重损失。在开辟德平、陵县一带地区,驻防于大宗家时,消灭了千余人的汉奸队,又连续打退敌之两次‘扫荡’后,为了成立政权机构,则在一地久驻不移,又未掌握确切的敌情,于是遭到敌之突然袭击,使部队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失。”
当时,五支队在大宗家一带的兵力分布是:支队指挥部、直属骑兵连、特务队和五团一营一个连驻前后侯家村,五团除二营跟随萧华活动外,龙书金和曾庆洪率团部特务连、三营十二连驻大宗家,一营驻赵玉枝家村,三营驻阎福楼村,总兵力达2000多人。龙书金的心情有些低沉,主要是因为一营营长谭端志的牺牲,眼前总有他挥之不去的影子。部队一驻扎下,龙书金跟曾庆洪就组织了追悼会,讲话中潸然泪下……而支队则在侯家村高搭戏台,汽灯高挂,举行军民联欢会,十里八乡的村民闻讯而来,锣鼓喧天,笑语欢歌,掌声如潮。
而此时,日军驻德州指挥部里同样灯明烛亮,驻德州日军旅团长安田大佐指着墙上的地图说:“根据确切的情报,八路军主力一部两千多人正驻扎在陵县大宗家一带,这里就是大宗家。”他身边聚拢着日军驻商河指挥官纳见、驻临邑指挥官渡边、驻宁津指挥官石黑、驻济阳指挥官雪野、驻盐山指挥官山田、驻东光指挥官藤井和驻乐陵指挥官宫泽文雄等人,“我们的计划是集中我军优势兵力,今夜出发,趁其不备,实施偷袭,让大宗家成为八路军的葬身之地。”
这些人大多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对安田如此兴师动众颇有微词。安田解释说:“八路军此部为挺进纵队五支队,系由八路军一一五师之一部发展而来,诸君不要忘记我五师团在平型关所遭之耻辱。据了解,该部曾参加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我五师团辎重部队之战役。因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要以报仇雪恨之意志实施这次行动。”安田所部正属于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五骑兵联队的一个大队,该师团是日军历史最老、战力最强的王牌师团之一,因人们所熟知的第十九任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而被称为“板垣师团”,其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恶罄竹难书。毋庸置疑,安田此次不惜投入重兵,是日本军人的荣誉心在作祟:他想凭此一战,为曾折戟沉沙于八路军的五师团挽回一点可怜的颜面。
是夜,2000余日军——包括步兵、炮兵、骑兵——分乘六七十辆汽车,以分进合击战术,向陵县大宗家一带悄悄移动。
军民联欢会开到半夜结束,人们意犹未尽地散去。
拂晓时分,龙书金被一阵狂乱的狗叫声惊醒,侧耳一听,还夹杂着零星的枪声!大叫一声“不好”,翻身跳下床,抄起腰带和手枪便往外跑,嘴里叫着通信员的名字。通信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像头浑身溜黑的小毛驴,闪烁着明亮的大眼睛,应声而到。
龙书金急吼吼地说:“快去通知政委给支队打电话报告敌情!”
“是!”小伙子一溜烟跑了。
龙书金带着几个人向村西十二连驻地跑去。到了村头,向西面一看,有些傻眼:透过灰蒙蒙的天空,黑压压的全是头戴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敌人,村外的小庙台阶上站着一个日军军官,冲着东方挥舞着指挥刀,更可怕的是日军步兵后边还游动着一队骑兵,战马鼻子里喷出一团团白汽,有的在原地滴溜溜地打转,有的用蹄子刨着土,有的昂首嘶鸣,一副急不可耐冲出来的样子。明摆着敌人想以迂回战术冲击我军阵地。龙书金深吸了一口气,毫不犹豫地命令十二连开火阻止敌人从容施展战术。十二连战士以高坡、洼地、树林、短墙等地形为掩护,向进犯之敌猛烈射击,啪啪啪亮嗓的是排子枪,嗒嗒嗒唱歌的是机关枪,轰隆轰隆咆哮的是手榴弹,日军一排排倒下,暂停了前侵的脚步。
驻侯家村的支队司令部正准备开饭,接到了五团政委曾庆洪打来的电话,报告说有敌情。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参谋长刘正当即跑到村西瞭望,果然见西方腾起一股很高的尘土,隐隐传来汽车马达的轰响和战马的叫声,不一会儿,就看清了最前边的日军骑兵,正以散兵队形向侯家村冲刺而来。片刻后,一辆辆汽车钻出尘土,满车厢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这时太阳已经升起,刺刀辉映出一片寒光。
我驻侯家村的兵力除支队司令部机关外有五团三营的一个连、一个骑兵警卫连,计400人。虽不明来犯之敌的数量,但应该不会少于此数。
日军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向村里逼近。
战斗打响了。
曾国华、王叙坤等人蹲在一堵矮墙后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商议对策。
曾国华说:“看来鬼子是豁出大本钱了!这种情况突围相当困难。”
“即使突围出去,转移也不容易,鬼子有马有汽车,速度快,机动能力强。我们跑不远就会被追上,被他们追上就糟糕了,在旷野里更是无险可凭……”刘正焦急地皱着眉头。
刘贤权说:“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我们手头的兵力也不算弱。等到大大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后,再组织突围。到时候敌人丧了元气,就不敢追了。”
“对!”王叙坤眉毛一扬,“依我看,立即命令赵玉枝家村和小王村的部队投入战斗,让他们袭击鬼子的骑兵,打掉敌人的这根长腿,我们就好突围转移了。鬼子步兵的两条腿想追上八路军连门儿也没有啊,他们的汽车在田野里也蹦跶不开!”
曾国华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安田大佐这是憋足了劲,要跟我们掰掰手腕子啊!这家伙曾经参加过平型关战役,明摆着是复仇来了,那咱就再好好收拾他一下!”当即摇电话给赵玉枝家村的一营营长温先星:“温营长,我命令你营联合小王村兄弟营的几个连,速到侯家来,打掉鬼子的骑兵队!有没有困难啊?”
“报告首长,没有!”温先星嘎嘣脆地回答道。
曾国华再给龙书金摇电话:“老龙啊,你们团能不能坚守上半小时再突围?”
龙书金回答:“没问题。”
那边温先星撂下电话,立即传令小王村的部队向赵玉枝家靠拢,两支队伍合到一处,在温先星的带领下,呈扇形队列在没长出庄稼的田野里向侯家村“切”过去。
侯家村外有一座大沙丘,安田的骑兵队就躲在后面。再不远处是一片枣林,安田大佐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安田依据情报将进攻重点确定为侯家和大宗家,对周边其他村庄之敌并未措意,认为只要攻其首脑,其手足必然救援,到那时再以骑兵队将援兵冲散,甚至吃掉。他怎么也没想到,八路军竟然在这种情况下,敢主动进攻自己的骑兵部队。温先星他们像一阵旋风说到就到,一眨眼就杀进了日军骑兵队里。战士们挺着刺刀冲着马肚子、马腿、马屁股一阵猛戳,马匹纷纷倒地,有的洒着鲜血悲鸣着跑了,马镫上还拖着日本兵的死尸。日本兵挥着马刀抵抗,马刀与刺刀碰撞,发出尖锐的声音。有的战士倒下了,依然挣扎着爬起来,死死抱住一条马腿,把马上的日本兵掀下来。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尸横遍野。这场近身肉搏战拼的不只是力气,更是意志,是精神,是信仰。日本武士道精神对阵中华民族的图存意志,野蛮对抗血性,仇恨碾压仇恨,结果是难分难解,相持不下。
正在侯家村指挥战斗的曾国华等人,听到村外沙丘那边传来激烈的厮杀声,知道是温先星部跟日军骑兵队干上了,此时不突围更待何时,当即传令将侯家村西、南、北三方面的兵力合于一处,用尚未投入战斗的骑兵警卫连作前锋,从村东突围出去。我骑兵连的战士早就憋了一股劲,一听命令,飞身上马,抽出明晃晃的马刀,抖动缰绳,率先冲向敌阵,支队机关和步兵紧随其后。日军忽见一支骑兵从天而降,顿时惊慌失措。翻飞的马蹄急速地踏过,一片鬼哭狼嚎。支队机关顺利突围而出。骑兵连乘势向日军骑兵队掩杀过去,日军只好分出一半兵力对付我骑兵连,一时腹背受敌,左支右绌。骑兵对骑兵,这是冀鲁边战场上从未有过的场景,人喊马嘶,人拼刀,马撕咬,遍地马蹄踩踏起滚滚黄尘。
安田大佐见骑兵队被夹击,形势危急,就登上一个高坡用旗语指挥进攻的步兵回援骑兵。却不想他这一举动,把自己暴露给了五支队领导。
曾国华说:“擒贼先擒王,我看先派人把那个日军指挥官干掉!”
一个步兵班和一个骑兵班应命而出,袭击日军指挥所。安田见状,慌忙上马,在卫兵的护卫下逃窜,没跑多远,被我军掷出的手榴弹炸中,像一个麻袋一样被强大的气流掀下马来,几片飞霰嵌进脑袋,顿时丧命。他一心想把大宗家变作八路军的鬼门关,却把自己送上黄泉路。
日军骑兵见指挥官丧命,一时不知何去何从,醒过神之后,纷纷撒马奔逃而去。
大宗家的形势比侯家更吃紧。
日军获悉大宗家为八路军团部所在地,集中了数倍于我的兵力从四个方向展开进攻。好在这时驻阎富楼的三营发现团部被困,主动派出十连,在连长张宝珊、杜指导员的带领下前来增援。龙书金正在村西指挥战斗,见到援军很高兴,握握张、杜的手,当即命杜指导员带两个排和机枪班到村东拒敌,张宝珊带另一个排到村南迎敌。他对两人说:“这是一场恶战,要打出我们团的威风来!”
“是!”两人同声应道,转身带队进入各自阵地。
日军多次强攻十二连阵地,在村口撂下一具具尸首,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与硝烟混合的气味。日军指挥官命炮兵以小钢炮和掷弹筒实施轰炸,一发发炮弹落在十二连阵地上,炸得泥土翻飞,房倒屋塌,砖瓦四溅,一棵棵大树也被炸倒。我战士被压得抬不起头,日军乘势掩杀过来。龙书金命战士们放弃村外阵地,退守村里,依托房屋、院墙跟敌人展开巷战。
龙书金带着几个人先后到村东、村南察看情况,敌军在这两个方向的进攻并不比村西弱,十连的压力很大。恰恰此时,龙书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团部与各营之间的临时电话线被敌人的骑兵冲断了。这时又传来村南情况吃紧的消息,龙书金带上通讯排的一个班跑到村南,赶紧布置火力,却遭到背后一股日军的攻击,只好边打边退往村东,跟杜指导员的队伍会合。杜指导员见敌人一步步逼近,红着眼,抱起一挺机枪,跳出掩体对着敌人“嘎嘎嘎”狂扫,打得日军滚的滚爬的爬,赶紧退缩回去。不知怎的,敌人知道了八路军的团长正在这里指挥战斗,即刻又组织起更强大的攻势,一拥而上,子弹像蝗虫一样覆盖下来,战士们被压制在地上,抬不起头来。龙书金见状,带上通讯排迅速转移到村外,占据一条壕沟,继续跟敌人周旋,一直坚持到午后一点多,日军的进攻却越来越猛烈。
龙书金的脸色严肃得像一块铁板,事后他跟人说:“当时对这场战斗会打出什么样的结局,心里一点底没有。”
曾庆洪趴在龙书金身边,朝外打一枪,也不看他,说:“老龙,我看我们得调一营过来支援,我到赵玉枝家村去一趟吧!”
龙书金朝外打一枪,也不看他:“不行!你是政委,派别人去吧。”
曾庆洪执拗地说:“这里少不得你,你留下指挥,我去!”
龙书金回头看着他,他的脸上含着淡淡的笑意,眼里似乎流淌着一条亮闪闪的小溪。曾庆洪握握龙书金的手:“老龙同志,这里的指挥任务就先交给你一个人了!”说完,他弯腰跳出阵地,钻进弹雨,向着赵玉枝家村的方向跑去。龙书金耳旁回荡着他的话音,木然地望着他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身影,突然看到他的身子在漫天尘土中晃了晃,一头栽倒。龙书金感到脚下的土地颤了颤,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怪叫:“曾政委!快快快,快去把政委救回来!”……
午后,日军又增援了六七百人,配备了八门小炮。龙书金眉头的疙瘩越拧越大,敌我实力悬殊,到底怎么打开困境呢?
这时支队通信员飞马跑来,传达曾国华的指示:为保存实力,命你部不要与敌人恋战,迅速撤出战斗。龙书金焦急地说:“你快回去向支队首长报告,说村里十连和特务连被敌人包围着,十二连只剩下一部分人坚持战斗了!”
因为团部与村里被困部队之间联络隔断,只好派通信员进村传达撤退命令,但在敌人的层层火力封锁之下,被派出去的通信员纷纷仆倒途中。这些通信员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刚才还在眼前活蹦乱跳的,一眨眼就被敌人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龙书金眼里喷着火苗,握枪的手啪啪响,牙咬得嘎嘎叫,他爆出一声粗口:“我操你八辈祖宗的小日本!”
“首长,派我去村里送信吧!我准能行!”一颗黑油油的小脑袋钻到他眼皮底下,一双黑水晶般的眼睛调皮地望着他,“大家都叫我机灵鬼,小日本的子弹又没长眼睛,肯定打不着我的呀!”
龙书金用力地握住他的手,他的手竟布满了与年龄不相称的老茧子,粗粗糙糙地拉人,这是一个平日里勤恳练习射击的“小鬼”。
这位小通信员像矫健的野兔蹿出战壕,随即又变成一条拧着身子游动的梭鱼,灵巧地穿行于敌人的火力网中,又或者突然匍匐前进,像一片小小的波浪滚动着,又或者打几个滚儿,像一只小刺猬团成的球。就在他快要爬上村外的土围墙时,他忽然像一幅没有钉牢的画儿被风揭下来,吹落在地……龙书金大叫一声,就在他要被悲痛和绝望裹挟的瞬间,这位小通信员一跃而起,像一朵小云彩飘进土墙里去了……龙书金长长吐出一口气。
后来了解到,这位小通信员进村后,找到了五团特派员谢甲树,传达了撤退的命令。十连和特务连正跟敌人打得难分难解,而且刚刚缴获了两挺歪把子机枪,还有其他一些弹药,一听让他们撤出战斗,思想上一时还拐不过弯儿呢:干吗撤退,打得正过瘾呢!虽然这么说,但撤退谈何容易,敌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往外冲了几次,都被密集的火力打了回来。
龙书金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知道里边的部队突围受阻,如果想接应他们出来,只有向支队求援。他不及多想,飞身上马,向着侯家村方向飞奔而去。
村里,十连和特务连跟日军展开了肉搏战。特务连的战士都是个顶个的精壮汉子,膀大腰圆,神威凛凛;他们除了佩带一支快慢枪外,都背插一把大砍刀。该连连长是个紫脸膛的大汉,一身的疙瘩肉,他舞动着大刀率先闯入敌阵,一阵东砍西剁,放倒了几个日本兵。日军见他勇猛,集中了七八个人端着刺刀围攻他,他毫无惧色,闪展腾挪,把大刀舞得像嗡嗡作响的纺车,不时传出“哎哟”“扑通”声,七八个日本兵的脑袋搬了家。他刚立定身子想喘口气,一眼瞥见七班长身后有个日本兵举起了刺刀,跑过去肯定来不及,随手一扬,大刀飞出,把日本兵的半个脑袋削了下来。“八路军连长飞刀斩鬼子”的故事在事后越传越神乎,说他的刀就跟牵着一根线似的,脱手飞出,砍死一个敌人,再自动飞回来,脱手而出,又斩杀一个,又飞回来……
日军尸体堵住了胡同,这些满脑子武士道精神的亡命徒仍然踩踏着同伴的身体往里冲……谢甲树怕我军消耗过大,下令放弃逐房逐屋的争夺,退守村子北部一座叫“保险院”的院落。这座“保险院”是大宗家乡绅宗子敬的庄园,既大又坚,原为防御土匪而用,当地人称“保险院”。宗子敬年已古稀,跑前跑后,张罗着给战士们准备饭食。日军一波波发动着攻击,一次次被击退。眼看我方弹药将尽,战士们急得直跺脚。宗子敬领着谢甲树来到后院的马厩里,挪开一口牛槽,再掀掉槽下的一块木板,露出一个大洞口,里面摆着十几只木箱,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条条钢枪和一箱箱子弹。他说:“你们为保卫国家豁出了命,我还能稀罕这点儿小玩意儿吗?”重新被武装起来的战士们生龙活虎般嗷嗷直叫,一排排子弹向冲上来的敌人倾泻……
龙书金见到曾国华、王叙坤等人汇报了大宗家的情况。
王叙坤说:“老龙你知道跟你交手的是鬼子哪一部分的吗?”
龙书金摇摇头。
“老对手了,板垣师团的残部窜到冀鲁边来了。”
“手下败将!”龙书金脱口而出。
“不能轻敌啊,他们可是要报那场战斗的仇哩!”王叙坤说,“你被困的那两个连怎么办?”
“你只要给我一个连的兵力,我保证能把他们接出来!”
曾国华说:“好!你先回去,援兵随后就到!我现给你凑,我手里的兵力也不富裕啊!”
龙书金快马加鞭赶回大宗家村外,不一会儿,援军也到了,但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他不由显得有些沮丧。
带队来的排长梁世淦不乐意了:“团长,支队长说实在抽不出来了,他们身边只剩一个排担任警卫了,够意思的了!”
龙书金一愣。
梁世淦又说:“首长,你别看我们是一个排,但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的人不少,打起来一个排绝对能顶一个连!”
龙书金点点头:“梁排长,你给我上的这课好啊!打仗绝不是光看人数,更重要的是士气和斗志。”
梁世淦带着一排人向村里冲去,与据守街口之敌展开近距离交火,接着是短兵相接。虽然战士们奋不顾身,一往无前,但毕竟敌众我寡,这次救援以失败告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过一秒就多一秒的牺牲,龙书金心急如焚,怎么办?他决定孤注一掷,把担任警戒的一班兵力调过来,再加上通讯班的十几个人,凡能参战的都加入战斗行列。他看着一张张被烟火熏黑的面孔说:“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如果这次救援不成功,十连和特务连可能就被小鬼子吃掉,这将是我们五团和五支队永远洗刷不净的耻辱!冲吧!”
这时,村里激烈的枪声响成一片,龙书金判断是十连和特务连正在组织突围,这个节骨眼儿拿捏得太准了!敌人在里外夹击下更加疯狂了,层层结队地从村里挺着胸端着枪向救援小队冲过来,一面冲一面喊着口号,日军指挥官挥舞战刀“嗷嗷”直叫。我方一机枪手见日军像疯狗一样冲上来,挺身端起机枪向敌扫射,前排倒下了,后排的日军踩着前排的尸体继续向前冲。
龙书金大喝一声:“投手榴弹,炸狗日的鬼子!”
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群,发出撕裂耳膜的巨响,将日军的队形炸出了一个缺口。这时被日军围困一天多的特务连和十连幸存的战士冲了出来,与龙书金会合一处。他激动地喊道:“快快!快向外边撤!”一百多名战士按照他的指挥冲过大宗家村外的旱河,向东北方向转移。
日军见网中的鱼儿逃掉了,气急败坏地冲向龙书金所在的阵地。这时他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他带着小分队迅速撤出战斗,退到村南一条沟渠近前时,不料埋伏在沟里的一个日军士兵冲他开了一枪,子弹洞穿了他的肩胛骨。他怒火中烧,右手甩出一枪,将那个日本士兵打翻在地。此后,他这支小分队也被日军冲散了。龙书金一人又辗转退至大宗家旱河,穿过沙滩,钻进一片黑幽幽的沙树林子,陆续遇到几个战士,这才听说团政治部主任朱挺先、特派员谢甲树都在突围战中牺牲了……
此时残阳泣血,大宗家旱河的沙滩上洇开着一朵朵桃花,风儿想拾起一朵,使使劲,却怎么也办不到。
大宗家一战,五支队主力团五团伤亡五六百人,遭受巨大损失,战后不久即将四团编入五团,以补充其实力。此战是八路军自平型关大战以后,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也是整个冀鲁边抗战时期打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五支队在没有预先准备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冷静调度,重创日军精锐之师,击毙包括安田大佐以下500多日军,打出了边区抗日部队的威风。据说这一仗也震惊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东京的广播电台为日军的这一惨败发出了哀号。就作战目的的达成看,日军这次精心策划的奔袭合围,未能达到歼灭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目的,可以说是失败了;就双方伤亡情况而言,可以说半斤八两,打了个平手。
1940年10月,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自庆云县到沧州至石家庄公路迎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大将,并陪同他到大宗家东一处墓地吊唁葬在那里的安田大佐和日军士兵。秋风萧瑟,雁阵横空,多田骏和本间雅晴沉默良久,不胜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