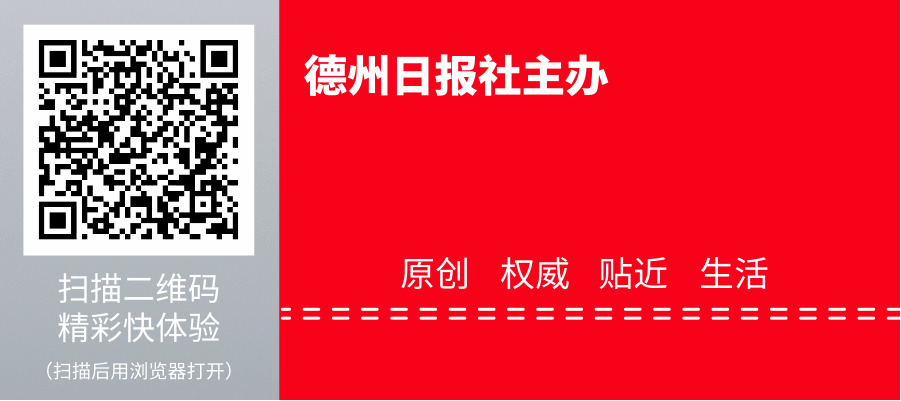1942 年 6 月 11 日,东光县盐场吴村的一个农家院。崔兰仙把一摞文件包进一块蓝头巾里,拿起桌子上一双没有缝好的小花鞋端详着,鞋头上各自绣着一只小蝴蝶,那粉色的薄翼似在轻轻扇动,带出丝丝凉风。崔兰仙抚摸着这两只针脚精巧的蝴蝶,嘴角漾出温柔的笑意。刚刚接到通知,要她去参加军政民联席会议,而且她也知道日军正在对冀鲁边区展开新一轮的“扫荡”。
1915 年,崔兰仙出生于盐山县旧县镇东街。1931 年,在盐山县城育才小学读书时,她听到日军侵占东北三省的消息,跟同学们走上街头散发抗日传单。当听到一位教师号召民众不当亡国奴的演讲时,她深深被其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打动,第一次流下了激愤的热泪。1932 年,她考入河北省立泊镇第九师范学校,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学生和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1935年,她毕业后回家乡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开展启蒙教育,宣传救国道理。崔兰仙性情刚烈,敢想敢为,当时的乡村封建思想很重,她这样抛头露面自然招来许多闲言碎语,尤其是婆婆家对她更是白
眼相向。1937 年 7 月 15 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旧县镇举行隆重的成立仪式,崔兰仙不顾婆家人的阻挠找到马振华,加入了抗日行列。1938 年 2 月,崔兰仙入了党,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战宣传工作。在她的鼓动下,她的娘家二哥参加了救国军,大哥为救国军送情报、筹粮款,嫂子和弟媳也参加了抗日活动,都先后入党。她的娘家成了党组织可靠的堡垒户。
1938 年 11 月,党组织派她筹建边区妇女救国总会。12 月底,边区妇女代表大会在旧县镇召开,她当选为冀鲁边区妇女救国总会主任。在她的积极协助下,盐山、庆云、乐陵、无棣、沧县、南皮、宁津等县的妇救会相继成立。崔兰仙时常打扮成逃难的难民或走亲戚的农妇,躲过敌人的耳目,穿梭忙碌于各地。她带着石磊光、邱岩桂创办了边区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解放》月刊,并经常告诫担任月刊总编辑的石磊光 :“刊物虽小,却代表着党对妇女工作的声音,每期的重要文章我必须亲自过目。”
崔兰仙的丈夫杨辛国出身于当地的乡绅家庭,在他们新婚不久就到宋哲元的部队当兵去了。卢沟桥事变后,他随国民党溃败的军队南逃,多次写信给她,指责她不守妇道,责令她脱离抗战工作。
崔兰仙看罢信,气愤难当,不仅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而且要他回乡参加抗日。杨辛国根本不听,最终她毅然决然与他断绝了夫妻关系。可怜撇下一个几岁的女儿景云,只好托给自己的母亲抚养。
崔兰仙极少回家看女儿,女儿的头脑中也没有关于父母的印象。
1941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母亲听说崔兰仙在离家 20 多里路的大桑树村,便拽着 6 岁的景云,一路小跑地赶到大桑树村。崔兰仙做梦似的看到母亲站在面前,背上背着一个睡着的小女孩,泪水哗地流下来,立即扑上去将景云搂在怀里,亲了又亲,亲了又亲,然后贪
婪地看着孩子的小脸,泪水还是扑簌簌地直流。
景云眨巴着眼看着这个陌生的女人,姥姥急声说 :“傻孩子,这是你娘啊,快叫娘!”
景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崔兰仙哽咽着答应了好几声。她给孩子拢着被风吹乱的头发 :“孩子,别怪娘啊!娘也想照顾你,可是小日本鬼子不让啊,他们抢占我们的土地,烧毁我们的房屋,杀害我们的人民,要不把这伙豺狼赶走,咱们是过不上好日子的。景云啊,你以后要学着做针线活,要自己照顾自己,别叫姥姥操心。”
母亲在一边陪着抹眼泪,看着女儿消瘦的脸颊,嗔怪道 :“看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这么长时间不回家,难道你们这些人都不要家了吗?”
崔兰仙破涕为笑,故意挺挺胸脯说 :“娘,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我们这些人怎么不要家了?打不走日本鬼子,国家都亡了,哪里还有家啊?”
老人说 :“你们啊,都会说大道理,俺一个乡下老婆子懂啥?可自己的闺女总得管管吧!”
崔兰仙说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我也想多管管她,现在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个用还忙不过来,只能累累您了。”
老人说 :“俺知道你们是干大事的人,可不嘟噜几句心里也坠得慌啊!”
崔兰仙放下孩子,找出一张纸、一把剪刀,在景云的小脚丫上比量着剪下一双小鞋样儿,说 :“景云听姥娘的话,娘给你做双小花鞋,保准你穿上要多俊就多俊!”
崔兰仙目送母亲和景云走出了村子,景云回头张望了几次,崔兰仙眼里的泪水又涌了出来。
房东刁文秀大嫂推门进来 :“兰仙,这当儿走挺危险啊,听说鬼子闹腾得厉害。”
崔兰仙咳嗽几声,说 :“这次开会肯定要研究‘反扫荡’的问题,你就放心吧。不过,我这里有些重要文件得先放在你家,你帮我把它埋好,过后我回来拿。”
刁文秀说 :“你这身子骨得悠着点,整天跟个老爷们儿似的跑啊颠的,哪受得了?”
崔兰仙说 :“没大事,我心里有底。咱村里的妇女工作还得加把劲,把姐妹们的干劲调动起来,给战士们多做点军鞋,好多战士的鞋底磨出了大窟窿。”
刁文秀说 :“嗯,你讲的那些道理姐妹们都挺爱听 ;俺再发动发动,争取入冬前做上一批棉鞋支援前线。”
崔兰仙说 :“好,我现在就走。”说完,把那双小鞋放进包袱里,打好结,穿上肩头,拉开门,风风火火地走出去。
当天晚上,崔兰仙在太平辛村遇到了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岫石、边区农救会主任姚任远。几个人紧急交换情报之后,连夜带着队伍向东南方向转移。此时的冀鲁边平原到处弥漫着庄稼生长的气息,夜虫伏在草间练习着生疏的小夜曲,星星静谧地洒下淡淡的光,又忽而诡秘地眨眨眼。崔兰仙、张岫石、姚任远夹在队伍中间疾走着。这是一支仅有 70 多人的小分队。没人说话,只有唰唰的脚步声。
根据情报,日伪军已经重兵布下了一张铁网,正在一点点地收紧,看似平静的夜晚就像无波的静水,表层之下暗流汹涌,埋藏着重重杀机。
12 日拂晓时分,天刚蒙蒙亮,队伍行进到东光县刘大瓮村一带,谁也不知道他们已经钻进了敌人撑开的“口袋”里。
崔兰仙等人正匆匆走着,前方传来了枪声,一名战士跑过来报告发现了敌情。张岫石侧耳一听,焦急地说 :“不好!我们落入敌人的包围圈了,兰仙你跟着队伍快向西北方向突围出去,我带一个班掩护!”
这时枪声骤然稠密起来。
崔兰仙抽出腰里的匣子枪说 :“张主任,你是部队的领导,部队行动不能没有指挥。你带大家冲出去,我来掩护!”
张岫石说 :“不行,打仗你没经验。”
崔兰仙说 :“老张什么时候了还争,你快带队伍走!”
说完,崔兰仙朝着敌人打了几枪,然后向西面的花子坟坟场跑去。张岫石命警卫班留下保护崔兰仙,然后隐没于庄稼地,悄悄钻出了包围圈。
日军被崔兰仙吸引过去,包围了花子坟。这里堆着一个个波浪似的坟头,荒草萋萋,野花招摇。朝阳正在升起,金光映在露珠里分外璀璨。崔兰仙伏在一个坟头后,眼睛紧盯着抵近的敌人,挥手一枪,喊声“打”,趴在坟后的战士们冲敌人一阵猛烈射击,把敌人打退了下去。崔兰仙拉拉背上的包袱,感觉到一个硬硬的东西,那是她给景云做的小花鞋啊!她嘴角轻轻颤抖了一下,或许已经意识到这双小花鞋和它所承载的母爱将永远没有归宿了……敌人又扑上来,崔兰仙沉着地瞄准射击,打倒了好几个日军士兵。子弹打光了,日军挺着刺刀逼过来,战士们相继牺牲于敌人的刀下。崔兰仙负伤被俘。
两个日本兵上前捆绑她,她奋力反抗,猛踢猛咬,大骂道 :“你们这些强盗!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中国人决不屈服!”
但她终究抵不过两个彪形大汉,被捆住了双手,托到一匹马上,准备带走。崔兰仙忽然一头栽下来,高呼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死不当俘虏!”日军一个小队长见状,走上前,伸手去撕她的嘴,却被她狠狠咬住了手指,好不容易拽出来,气急败坏地抽出战刀,向着她的腹部连捅几刀。崔兰仙倒在血泊中,向着敌人怒目圆睁着,停止了那颗为民族解放而跳动的心脏,时年 27 岁。崔兰仙的身下压倒了一片野菊花,蓝的,粉的,浅红的,金黄的,争相绽放,她背后的包袱已被刺刀划破,那双小花鞋溜了出来,鞋头上的一双蝴蝶在花丛里翩翩飞舞着……
6 月 19 日夜,东光县大单家村,一地委、一专署机关临时驻地,灯光明亮。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杜子孚的心紧作一团,不断汇总上来的情报表明 :日军这次“扫荡”规模之大、部署之严都是少有的,而且重点区域就在一分区。一地委、一专署的领导层对“反扫荡”存在的分歧比较大 :有人认为这一带北有大洼,南有鬲津河,交通沟纵横交织,我们既熟悉地形,又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可谓占尽了地利和人和,可以与日军放手干一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再走 ;有人认为这次日军目的性强,明摆着是冲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来的,咱们再去硬碰硬,肯定要吃大亏,应该抓紧转移到安全地带。
最后,大家注视着杜子孚,他作为一地委书记、一军分区政委到了必须表态的时候 :“同志们,不能再争下去了!情况紧急,不能把时间消耗在这种无谓的争执上。根据最新情报,周围据点的敌人正向大单家扑来,敌人的合围已经开始,我们必须马上转移,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冲出包围圈。”
一地委组织部部长邸玉栋说 :“我完全同意杜书记的意见。我建议机关、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突围。”
杜子孚下令 :“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组织转移,沿着往三营盘村的交通沟,向鬲津河靠近,抢占河堤,渡河向东转移!”
夜色中,杜子孚和一专署专员、一军分区司令员石景芳带着一部分机关干部、战士沿道沟跑步前进 ;邸玉栋带着部分机关干部沿另一条道沟转移 ;与此同时,驻小单家村的一地委青救会、鬲津县青年连在燕明、鲁英带领下闻讯向黑龙沟方向转移。
杜子孚 9 岁时发生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为他的一生定了调 :那年,他正在大白庄私立小学读书,因为喜欢提课本以外的社会问题请老师解答,被一位姓冯的老师用藤鞭敲了两次脑壳。他捂着火烧火燎的疙瘩,一肚子的愤懑,一肚子的不服气。后来冯老师逢人就说:“杜子孚的脑后长着反骨,小小年纪就不安分!”杜子孚果然不是顺民,没读完一年就炒了冯老师的鱿鱼,回到本村南皮县后郑村跟着柴先生上学,后又就教于张连福先生。
1931 年,他考入南皮县黑龙村县立第二高小。“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带同学们到附近的集市上演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1934年,他高小毕业,怕父亲让他守业治家,没有回家直接蹽到天津,投考了河北省立第一师范,拿着通知书回家,来了个先斩后奏。即使这样,父亲还是不应允。他就动员族叔们给父亲“解疙瘩”,说得父亲面子上下不来,只好答应了他。父亲狠狠心,卖了三亩地,凑够学费,供他上学。
在省立一师期间,杜子孚的思想发生巨变,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1935 年 12 月,他带着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北风呼啸,杜子孚向街边的店铺借了一条板凳,跳上去,挥舞着拳头,发表了一通振奋群情的演说。同学们被他的演讲感染,将他高高地抛起来,接连几次,气氛极其热烈。他也“荣幸之至”地上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共党嫌疑犯”的名单,准备将他逮捕入狱。
学校党组织出于保护进步学生的考虑,劝说他弃学回老家躲避。
不久,他又考上了泊镇省立第九师范,随即投入了新的学生运动。
1937 年 9 月 18 日,日军占领泊镇。杜子孚毅然辍学,几经周折,找到津南党组织负责人马振华,正式加入了抗战的队伍。他接受任务回南皮县筹建了战委会,任主任。1938 年前后,抗战经费很困窘,他动员父亲说 :“咱把家里的三亩八分地典出去吧!”父亲牛眼一瞪 :“啥?那可是俺的命根子!”他说 :“现在队伍缺衣少鞋,许多战士受了伤,没钱买药治疗,都硬扛着!你就忍心了?”父亲垂着眼皮,低头抽烟。他又说 :“咱典出去,再租回来种,中间一转就是活钱了。
再说,你老人家支持抗日,等打跑了鬼子,还能没你种的地?”老人一百个不愿意地典出了地,把钱给了杜子孚。也是这年,杜子孚派一位姓张的同志去天津执行任务,为了给老张凑路费,他悄悄把自己的棉袄当了。这种钱老张哪能接啊?他一把塞到老张怀里 :“拿着!穷家富路嘛!”
1941 年下半年,杜子孚调任一地委书记兼一军分区政委。
天色放亮,平原上飘浮着淡淡的雾气,没有风,半人高的玉米纹丝不动,叶片披着露水 ;不远处的村庄朦朦胧胧,几处高丘上的树林影影绰绰,跟水墨画似的描在那里。四周如此寂静,静得人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杜子孚有种不祥的预感,直起僵硬的腰板向前方望去,前边的道沟伸入一片庄稼地里,看不到头。
他对石景芳说 :“老石,天快亮了,我们得加快速度,越快越好!”石景芳压低声音对通信员说 :“命令前边的警卫连,全速前进!”通信员跑走了。
突然,前面响起嘎嘎嗒嗒的机枪声,杜子孚大叫一声“卧倒”,猫着腰、提着枪向前跑去,石景芳紧随其后。警卫连的战士被敌人压在道沟里,组织不起像样的火力,只能零星地还击。杜子孚和石景芳紧贴道沟壁站住,探头往外张望,耳边嗖嗖飞过几粒子弹,赶紧缩回头。杜子孚说 :“敌人正在向这里聚集,必须立即突围!老石,我带警卫连冲过去,你带人跟上!”杜子孚挥手叫过警卫连长,命令把两挺轻机枪对准敌人火力稠密处猛打。趁着敌人火力被压制住的空当,他跃出道沟,带着警卫连向敌人阵地冲去。战士们边跑边打,撕开了一个缺口,掩护机关干部快速通过。
杜子孚、石景芳带领队伍又跳进一条道沟,继续向鬲津河岸转移。身后的敌人咬得很紧,不时放冷枪。队伍渐渐接近河岸。此时日上三竿,薄雾顿消,杂树丛生、野花遍地的堤岸已在眼前。鬲津河的水声隐隐传来。如果能翻过大堤,就可以凭借此险,组织起对追踪之敌的有效阻击。警卫连刚挨近堤下,堤上就冒出密密麻麻的钢盔,几挺机枪铺天盖地地扫射下来,战士们倒下一片。
杜子孚和石景芳一商量,石景芳带一部分人掩护,杜子孚带一部分人转移。
杜子孚带队向西北方向边打边撤,进入“四柳林”一带。“四柳林”是赵家柳林、孙家柳林、王家柳林、宫家柳林四个村子的合称,时属鬲津县管辖。鬲津县设立于 1940 年 6 月,由宁津、南皮、东光、乐陵四县的边沿地区组成。“四柳林”地势低洼,盐碱,瘠薄,
适于植柳,村周围、漫洼地随处可见柳树的婀娜身影,“柳林烟树”的景致颇为当地人称道。
杜子孚喘息未定,石景芳也率队赶上来,但突围时中弹负伤,胸前血迹一片。
杜子孚来不及询问石景芳的伤势,说 :“老石,我看我们掉进敌人的包围圈了,往哪儿跑都有敌人,得做最坏的打算了。”
石景芳喘着粗气说 :“杜书记,我们从干革命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党和人民。”
杜子孚说 :“老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共同的信念。”
石景芳说 :“我听着崔达家村方向没有枪声,我们就向那个方向突围吧!”
杜子孚点点头,带领队伍跳进王家柳林村至崔达家村的南北道沟里。
队伍刚到崔达家村到刘连庄的东西道沟前,隐蔽在沟里的一股日军突然开火。我军战士纷纷倒下。杜子孚带领一个班顶住前面敌人的进攻,石景芳带一个班顶住身后的敌人,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其他人趁机从敌人的缝隙间冲出去,边打边撤。
敌人一层层包围上来,密集的子弹疯狂地射来,我方不断有战士牺牲。杜子孚、石景芳带着战士们顽强还击,一次次打退了敌人进攻,最后子弹打光了。杜子孚和石景芳跟战士们背靠背围成一个圆圈,挺着刺刀,毫不畏惧地面对着逼上来的敌人。
杜子孚喊道 :“我们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死是中华民族的鬼魂,一定要和敌人拼到底!”
硝烟在他们面前飘荡,怒火喷出了双目,是时候了,是到了给祖国一个誓言的时候了,是到了给祖国和党一个血洗的誓言的时候了!
狰狞的日军士兵知道他们的枪膛已空,这些人里有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妄想生擒活捉几个,便有恃无恐地围上来,却遭到了最强悍的抵抗——杜子孚和石景芳带领十几名战士用刺刀、拳头、砖头甚至牙齿,向日军宣示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意志。杜子孚见一个日军士兵挺着刺刀向石景芳的后背刺去,失声喊道 :“老石!敌人——”随即抄起一块砖头砸过去,将其打倒。忽然他身子一侧歪,看到自己胸前穿过一个挑着血丝的刀尖。他捂住伤口,艰难地扭转身子,目眦欲裂,怒视敌人 :“狗——强——盗!”随后倒在道沟里。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眼投向了高天流云,那浩瀚的蔚蓝是灵魂的栖息地,站在云端可以恣意地俯瞰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可以将目光锁定在那个叫后郑村的邮票般大小的故乡,可以俯下身子亲吻这里的田野、树林和河流,然后蜕变成一粒水滴落下来,把自己结结实实地嵌进大地深处……
石景芳眼睁睁看着战友倒下去,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想要抱起他,就在他的手指将要触到杜子孚的衣襟时,敌人的刺刀也穿透了他的胸膛,他慢慢地慢慢地倒在杜子孚身旁。
津南地区老牌革命者、一地委组织部部长邸玉栋为掩护同志们撤退,也在此次“扫荡”中壮烈殉国。此役另有一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专署财政科科长陈介清、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徐镜尧、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以及其他干部、战士300 多人牺牲。被俘 40 多人无一降敌,全部遇难。
早在 1942 年 4 月,冀鲁边军区和教导六旅就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 :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 3 万日伪军,将于 5 月 1 日向冀中根
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军委命你们派部队到津浦路沿线接应冀中军区突围出来之部队。接着,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针对日军此次“扫荡”专门电示冀鲁边区 :“冀鲁边的位置十分重要,日寇很可能在‘扫荡’冀中以后,复来‘扫荡’边区,尤其是津浦路沿线……你们务必作好准备!”
冀鲁边区军区领导紧急磋商后,决定 :十八团在团长杨柳新、政委杨爱华的带领下,移动至津浦路沿线的东光、南皮一带,接应冀中部队 ;教导六旅主力部队和各分区的地方武装,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以防遭敌人围攻。军区的几个领导人做出相应分工 :黄骅带一部到盐山、庆云、乐陵活动 ;周贯五、卢成道带一部活动于吴桥、沧州 ;邢仁甫以自己刚回来不熟悉情况为由,提出带旅部机关到新海县冯家堡、狼坨子等海边渔村活动。
5 月 1 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几万大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毁灭性“大扫荡”。冀中八分区后勤人员、教导队 500 多人,武装宣传队 70 多人,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及冀中军区主力二十三团,先后跳出敌人包围圈,越过津浦路,进入冀鲁边区,被边区部队护送到新海、盐山的海边隐蔽。
不出所料,5 月 26 日,冈村宁次飞抵德州。6 月 9 日,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二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两万多人,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等铁路沿线据点出发,驻沧州日军联队长古川部及大批伪军从沧州出发,由南、北两线向东推进,以多路奔袭战术,对东光、南皮、宁津、庆云等地实施“拉网包围”,于第二天拂晓完成包围圈。然后,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此次“扫荡”和反“扫荡”斗争持续 50 多天。日伪军合击圈东起南皮县沟章寨子,西
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堆镇,北至宣惠河畔的刘夫青村,方圆60 余里,核心地带为“四柳林”地区。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全被“网”进了包围圈。
从此,“四柳林”这个美丽的名字被笼罩上一抹厚重的悲壮的血色。损失是空前的,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机关近乎“归零”。
冀鲁边区党委迅速做出了重建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的决定,抽调人员配齐了班子,由彭瑞林接任一地委书记,王亦山接任一专署专员,曹戎任地委副书记。
“四柳林”的血迹未干,7 月 2 日,教导六旅十八团又在沧县大七拨一带被日军合围,团长杨柳新殉国,全团损失近三分之一。
整个边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恰恰这时,正在宁津、乐陵一带忙着反“扫荡”的周贯五接到两封电报,一封是黄骅的,一封是邢仁甫的。黄骅已带部队从庆云、盐山撤往新海县,与邢仁甫所带旅部机关会合。黄骅在电报里说邢仁甫胆小怕死,只顾经营个人的安乐窝。邢仁甫则指责黄骅骄傲自大、主观武断。周贯五拿着两封电报,脸上霜气凝重,这可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尤其在这种艰危的形势下。
周贯五跟卢成道商议后,决定率军到旅部所在的望子岛做上一回“和事佬”……